遇见、依止、随修法(遇到依止师就是自己成佛的时节到了)

我与佛有缘,我真心想学佛,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自己一直没遇见有缘人...请有缘的朋友给我一些建议
阿弥陀佛!随喜赞叹师兄的正心正念。
学习佛法,首先要知道佛所讲的基本和核心是什么。不论修行任何法门,这些都是基础!其中包括: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念处是非常实用的修行方法,果能依次第如理观照,深悟其理,则看破一切虚妄颠倒,必定解脱六道。
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是佛留与我们末世众生验证佛法与否的标准和依据。
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是佛为我们总结的修行顺序和次第。此八正道依次生起。我们要学习佛法,必须先有正见,有了正见,才可能有正的思维。有了正的思维才能产生正语、正业及正命。有了正命才是真正的正精进,否则,没有正的方向,就算是再精进,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必不能导至正念,不能得以正定!
四依止:依智不依识,识义不依言,依法不依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此四依止,如果我们能深刻体悟,如实依止,能保证我们不入邪途,不堕险坑!
师兄,若是感觉这些最初接触,比较难懂,在下可以推荐你观看阅读慧律法师的新浪博客,上面有许多关于讲法的内容,可供学习。慧律法师也是一位见解非常正的正法师父,师兄可以放心学习!
另外,师兄也可以百度视频搜索:普愿讲堂,推荐师兄观看《佛弟子的正知正见》、《陀佛三法印》以及《如何逐渐步入佛法解脱》系列,深入浅出,比较容易懂!
略论》依止善士》略示修法》未修中间--济群法师讲解
原文链接
四、未修中间
未修中间,指两次修习的间隔。虽说是“未修”,但在此期间并非不必修行,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修行。换言之,是座下的修行,生活中的修行。
在我们的观念中,修行通常是指禅修、念佛等特定形式。但座上时间毕竟有限,更多时间还是在座下。如果把座上和座下打成两截,真正可以修行的时间就少得可怜了。常听很多人说:虽然每天都在打坐、念佛,但上座后觉得很难静下来。之所以会这样,正是由于平时没有良好的用心习惯。因为思惟是相续的,有惯性的,平时特别在意的事,在座上构成的干扰也最大。当情绪被某些事调动起来,即使上座后,心也是难以收回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生活中也要保有正知正念,这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在座上的观修效果。戒律的作用,正是帮助我们建立如法的生活,这也是心能够长时间安住于善所缘的前提。
礼拜、经行、念诵等等,虽有多门,其主要者,若仅于正修时精进,未修间则于其所修法不住念知,多诸散乱者,则生效甚微。
故虽未修之际,亦应读诵、观览关于此类之教法,并数数忆念之,广修助道顺缘,勤忏障道罪垢。且于一切之根本,即本所受之戒,宜善护持。
复应于止观易生之四因,善修习之。
首先,总的说明未修中间应当如何调心。很多人之所以修行不得力,主要就是因为平日不能善用其心。心念像流水一般,不会上座后就立即切断,自动改道。这种“截断众流”的功夫,一般人并不具备,这就必须依靠平时的守护。在座上修什么,也要将这一用心带到座下。
“礼拜、经行、念诵等等,虽有多门,其主要者,若仅于正修时精进,未修间则于其所修法不住念知,多诸散乱者,则生效甚微。”不住念知,即不住于正知正念。修行法门虽有很多,如礼拜、经行、念诵等,但如果只是在正式上座修行时精进用功,平时却不能安住在与所修法门相应的正知正念中,妄想纷飞,散漫放逸,那么修行必然收效甚微。
“故虽未修之际,亦应读诵、观览关于此类之教法。”因此,虽然不是正式修法的时间,也应念诵或阅读与此相关的经论。比如修依止法,应该反复念诵《事师法五十颂》等相关典籍,反复思惟其中深义,从而对依止功德和不依止过患获得定解,成为确定无疑的认识和想法,而不仅仅是停留于概念性的了解中。很多佛子都知道因果、无常等教法,但这些认知对我们的人生有多少影响?是这些教法没有力量吗?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对因果和无常没有形成坚定不移的定解。似乎这些教理只是用来说的,只是一种抽象的、用来解释世间现象的理论,是现实生活之外的概念。
“并数数忆念之,广修助道顺缘,勤忏障道罪垢。且于一切之根本,即本所受之戒,宜善护持。”获得定解后,还应当时时忆念,使这些观念深深扎根于心田。同时,广泛修习并创造有利修行的顺缘,精勤忏悔障碍道业的罪业。对于一切修行的根本,也就是我们所受持的戒律,更须勤加守护。戒是无上菩提之本,也是正顺解脱之本,是修习任何法门都绕不开的基础。否则,很容易偏离方向。
“复应于止观易生之四因,善修习之。”所以,应该对有助于止观生起的四种助缘善加修习,分别是守护根门、正知而行、于食知量、悎寤瑜伽,相关内容在《瑜伽师地论》中有详细介绍。
1.守护根门
谓依于根尘生六识已,再于识所了别之悦意六境及不悦意六境生贪嗔时,当好自防护,莫令生起。
第一,守护六根门头。六根分别为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们接受外部信息的六个窗口。眼睛接受颜色的信息,耳朵接受声音的信息,鼻子接受气味的信息,舌头接受味道的信息,身体接受感觉的信息,意识接受诸法的信息。佛教认为,世间万相皆可统摄为法,包括我们看到、听到、可以言说和无法言说的一切。前五识所缘为现量,而意识所缘境界最为广泛,称为法尘,在认识作用上有现量、比量和非量三种。
“谓依于根尘生六识已。”当六根接触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时,会生起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说法。按唯识观点,每个识的生起,根和尘只是其中的重要条件,还须其他因素的共同成就。如眼识的生起要有光线、距离等九个条件,所谓“眼识九缘生”。
“再于识所了别之悦意六境及不悦意六境生贪嗔时,当好自防护,莫令生起。”在识所缘的境界中,既有我们喜欢的六种境界,也有我们不喜欢的六种境界。面对悦意和不悦意两类境界,内心会产生不同反应,对悦意之境起贪,对不悦意之境起嗔。守护根门所做的,是在这个关头保持正念,保持觉照,不使贪嗔之心生起。
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相应定力,还是应该以远离为上。出家众应选择清净丛林修行,在家众则应选择正命而如法的生活。否则,时常接触不良境界后,难免把持不住。当然远离并非究竟解决之道,具备定力后,还是应该以观照力来面对,这样才能真正不被境界所转。
2.正知而行
如《入行论》云:“身心于时时,应数数观察,专务于此者,即护正知相。”此谓身等于彼彼事转时,须依正所了知之应作不应作而行。
第二,正知而行。
“如《入行论》云:身心于时时,应数数观察,专务于此者,即护正知相。”正如《入行论》所说的那样:对于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应当时刻保持智慧的观照,能够专心于此的人,就是在护持正知正念。
“此谓身等于彼彼事转时,须依正所了知之应作不应作而行。”这就是说,当身、口、意三业面对相应境界时,应当依正念明确了知,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每天,我们都要说很多话,做很多事,但往往是随着念头或所缘境跑来跑去。某个念头现起,立刻随之而去,并落入相关情绪,却很少反省这个念头如法与否,这个行为正当与否。
正知而行,就是提醒我们以智慧观察每个起心动念和所作所为。对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时时都能了了分明,而不是被念头驱赶着忙来忙去,却不知自己忙些什么。一旦正知正念力量生起,情绪对我们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
3.于食知量
改正过多过少违量而食之串习,总以无碍修善为度。又修于食爱著之过患,以无染心及为饶益施者,并念身中诸虫,现以食物摄受,俾未来世亦得以法摄而化之。又念,为作一切有情义利而受其食。
《亲友书》云:“受餐如服药,知量去贪嗔,非为肥骄傲,但欲任持身。”
第三,是关于饮食的修行。饮食是滋养色身的重要手段,经云:“一切众生,皆依食住。”有情生命需要食物来维系,包括段食、触食、思食、识食四种。段食,即分段而食,是我们平常受用的饮食。触食,即身体对环境的感受,那些恶劣环境也是会影响身心健康的。思食,即意志,是我们生活在世间的动力。有些人临命终时,因为心愿未了,往往能支持很长时间。而在生命延续过程中,“我想活着”这一念头则会牵引我们不断投生。识食,生命延续需要有识的执持,一旦识离开后,身体就成为没有知觉的尸体了。本论的“于食知量”主要是指断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吃饭成为修行呢?
“改正过多过少违量而食之串习,总以无碍修善为度。”对于日常饮食,我们要改正吃得过多或过少的习惯。究竟应该吃多少,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总之,应该以不妨碍修行为标准。不少人遇到好吃的,就会暴饮暴食,结果不仅消化不良,还会引发昏沉,影响修行。当然吃得太少也不行,因为色身也是需要食物滋养的。
“又修于食爱著之过患。”此外,还应观修贪著食物的种种过患。一是金钱的过患,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大量消费,就必须为此辛苦工作。一是色身的过患,过量饮食会给消化系统造成极大负担,有损健康。其实,再精美的食物,只要嚼了吐出来,就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垃圾,实在没什么可贪著的。吃肉,更等于在分食动物尸体。丰子恺曾经有过一幅题为“开棺”的漫画,画中就是一把刀在打开肉罐头。我们觉得肉罐头是食物,可仔细想想,不就是装尸体的棺材吗?
“以无染心及为饶益施者,并念身中诸虫,现以食物摄受,俾未来世亦得以法摄而化之。”我们应该以利益布施者的清净发心而受用食物,并想到那些生活在我们体内的寄生虫,观想自己正以食物摄受他们,由此结下善缘,未来能以佛法摄受并度化他们。经云:“色身为虫聚”,只有我们受用食物,它们才能因此受食并存活。
“又念,为作一切有情义利而受其食。”我们还应该观想,受食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借假修真,以这个色身完成修行大业,最终利益一切众生。这样吃饭,就是在修行了。
“《亲友书》云:受餐如服药,知量去贪嗔,非为肥骄傲,但欲任持身。”《亲友书》说:吃饭应该像吃药那样,按一定的量服用,远离贪嗔之心。因为吃饭并不是为了长养我执,而是为了使色身正常运转,担负修道使命。一般来说,我们对吃药是不会贪著的,但为了健康也是不会拒绝的。如果能以这样的心态吃饭,就能有效去除对食物的贪嗔之心。
可见,吃饭能否成为修行,关键就在于对待饮食的心态。丛林的斋堂又名“五观堂”,也是要求僧众在受供时“食存五观”。五观的内容是:
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想着自己所吃的每一口饭,会有许多人付出辛勤劳动。我们不耕不织,却在此安然享用,由此生起感恩之心。
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同时还要想想自己有什么资格和德行接受他人供养?如果德行未具而受供,是有损福报的。所以我们不仅要惜福,更要培福。如果不慎将现有这点福报耗尽,修道障缘将会更多。
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用餐时应该保持观照,不起贪嗔。这是饮食中常有的两种状态,合口味就拼命贪吃,不合口味就心生烦恼,这就被舌根所转了。
四、正事良药,为疗形枯。饮食不是为了长得好看,也不是为了贪著美味,而是为了治疗饥渴之病。戒律中,将饥渴等身体所需称为“故病”,即与生俱来的疾病,食物不过是疗病良药。
五、为成道业,应受此食。我们吃饭,是为了修行、为了成就佛道、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如果有这样的发心,无论吃什么都消受得起。否则,在寺院享受十方僧物时,自己还是要掂量掂量的。
以上五种观想都是帮助我们在吃饭时提起正念。当然,其中有一些是特别针对出家人而说。但核心有两点,一是远离贪著,二是端正发心,为利他而吃,这也是每个在家众应有的认知。
4.悎寤瑜伽
勤行悎寤瑜伽,及睡眠时应如何者,《亲友书》云:“精勤度永日,及初后夜分,眠梦犹存念,勿使命虚终。”谓昼夜永日及夜之初后二分是正修时。若修习之余,在经行宴坐中(应以精勤)净除五盖,令其具义利也。睡眠者,系休息时。虽然,亦勿令其无义空过。
此中身之威仪者,于中夜时右胁而卧,左腿压右上,如狮眠伏。
云何正念?谓安住正念,于昼日中所修何种善法,随熏习力强者而系念之,乃至未睡之间,追随依止。如是,虽睡还同未睡,亦能修习定等善行。惑起觉知者,依忆念之力,任起何种烦恼,即须了知而不忍受,务令伏断。
思惟起想者,先可预想至彼许时当起。
第四,关于睡眠时的修行。在我们的一生,睡眠占用了相当惊人的时间。如果一天睡八小时,就会睡掉人生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能利用睡眠修行,是对生命的极大浪费。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从此夜不倒单,而是要把修行时的正知正念带入睡眠,使之不要中断。很多人可能觉得难以做到,其实,心是具有这一作用的。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如次日有要事必须早起,如果对此高度重视并反复提醒自己,到时间便会自动醒来。再如全身心忙于某事时,梦中也会出现相关内容,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果我们能将白天培养的正念带入睡眠中,那么睡觉也是修行。
“勤行悎寤瑜伽,及睡眠时应如何者。”悎,同觉。寤,睡醒,又同悟。瑜伽,意为相应,最高的相应,是和空性的相应,和佛菩萨的相应。我们在睡眠中也应保持精进并与觉悟相应,那么,睡眠时又该如何修行呢?
“《亲友书》云:精勤度永日,及初后夜分,眠梦犹存念,勿使命虚终。”《亲友书》说:应在精进修行中度过白天的所有时间,以及初夜(十八至二十二点)和后夜(凌晨两点至六点)。在睡眠乃至梦中,依然要保有正念,这样才能不使生命虚度。正如佛陀在《遗教经》所说:“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
“谓昼夜永日及夜之初后二分是正修时。若修习之余,在经行宴坐中净除五盖,令其具义利也。”宴坐,静坐、安坐。五盖,指贪欲、嗔恚、睡眠、掉悔、怀疑这五种覆盖心性、令善法不生的烦恼。整个白天和初夜、后夜两个阶段,都是用功办道的时候。而正式修行的间歇,在经行或安坐时,也应避免贪欲等五种烦恼的生起,为修行营造心灵环境,这样才能获得佛法利益。
“睡眠者,系休息时。虽然,亦勿令其无义空过。”睡眠,是缓解色身疲劳的方式,能够令身心得到休息。虽然这样,我们也不能令睡眠中的那些时间毫无意义地虚度。
“此中身之威仪者,于中夜时右胁而卧,左腿压右上,如狮眠伏。”身威仪,即如法的仪态。睡眠时,身体应有的如法仪态是什么呢?在中夜休息时,应向右侧卧,左腿安放在右腿上,像狮子睡觉那样。睡眠姿势有多种:仰卧是天人的睡相,俯卧是畜生的睡相,左卧是贪婪的睡相。而右卧则是吉祥卧,可防止妖魔侵扰,不起噩梦。
“云何正念?谓安住正念,于昼日中所修何种善法,随熏习力强者而系念之,乃至未睡之间,追随依止。”什么是正念呢?就是令心安住于正念。我们应当按照白天所修的法门,选择其中修习得较为纯熟者,以此作为睡眠时的系心之处。当我们准备睡觉而尚未入眠时,就应该忆念这一善法并安住其上。
“如是,虽睡还同未睡,亦能修习定等善行。”如果能够这样,虽然在睡眠中,心行仍在产生作用,仍能修习禅定等各种善行。之所以选择“熏习力强者”作为睡眠时的系念,关键在于睡眠时用功难度较大。平时有十分的功夫,睡眠时只能用上一分。如果没有平日的积累,睡眠时是不太可能继续用功的。
“惑起觉知者,依忆念之力,任起何种烦恼,即须了知而不忍受,务令伏断。”当烦恼现起时,应该依正知来保持觉察。无论现起什么烦恼,都要有清晰的觉知,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进而,还要以觉照力照破并断除烦恼。凡夫因为缺乏观照,烦恼现起时往往一头栽入其中,不能自拔。如果具有“惑起觉知”的能力,烦恼的影响就会随之减弱。
“思惟起想者,先可预想至彼许时当起。”睡下时,应当提醒自己明天几点起床,到时就自觉起身。如果没有这一提醒,很可能一觉睡去,就睡到日上三竿,浪费大好时光。
如果能将守护根门、正知而行、于食知量、悎寤瑜伽四项行持运用到生活中,根境相对时看住六根,行住坐卧中保有正知,同时在饮食和睡眠时安住于法,那么,我们就无时不在修行了。用心纯熟之后,座上座下便能打成一片。座上修行无非是止和观,无非是培养正知正念。这样的训练,座下同样可以进行。两相呼应,修行才容易真正契入。否则,每天花一些时间禅修,其他时间却在贪嗔痴中,等于以一小时培养的正念来对抗十多小时培养的妄念,成功的希望自然渺茫。修行不是一项独立工作,而是贯穿于我们的整个人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需要使生活成为修行,或是为座上的修行服务。
如上所言之一切修法,唯除正行中之少分不共者外,余之加行、正行、完结及座隙等中当如何作者,自此段起乃至修观,勿论修习何种所缘行相,于一切处皆应加入焉。
这一段是告诉我们,以上所介绍的“略示修法”不仅是为依止法安立的,也可适用于其他一切法门的修行。事实上,世间任何事业的成就都离不开加行、正行、结行这些步骤。西园寺筹备三宝楼工程期间,为做好调研工作,前后花了数年时间考查相关建筑,又请了数批工程师进行设计,几易其稿,这些属于加行部分。正式动工又花了两年时间,这一过程就是正行。最后则要举行落成典礼,为结行。可见这一套路既有很强的实用性,也有广泛的适应面。
“如上所言之一切修法,唯除正行中之少分不共者外,余之加行、正行、完结及座隙等中当如何作者,自此段起乃至修观,勿论修习何种所缘行相,于一切处皆应加入焉。”座隙,未修中间。此段,这里指依止法。以上所介绍的一切修法,除正行部分略有不同外,其余部分,比如在加行、正行、结行及未修中间时应该如何修习,从此处所说的依止法开始,直到修习止观,不论修行所缘境是什么,都应该在修习过程中加入这一套路。也就是从加行进入正修和结行,同时保持如法的生活状态,为修行营造心灵环境。
“略示修法”的套路不仅适用于《道次第》,也适用于其他一切法门的修学。因为任何一种教理都要落实于止观,才能在我们的心行上产生作用。如果所学不能落实于止观,转化成为正念,就只是理论而已,面对烦恼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不少学者把佛法当做学问研究,说起来虽也头头是道,做起来却往往一无是处。根本原因,正是所学未能成为心行力量。
略论》依止善士》略示修法》正行--济群法师讲解
原文地址
二、正行修法
加行之后,将进入正行的修习,从总说和别说两部分加以说明。
1.总说修法
所谓修道者,即于善所缘,如欲而能令心安住之谓也。若于所缘随意修习,依自己所想之数目与次第而修者,从初即养成任意之习惯,将至一世之善行无成,反成有过。故最初无论修习何种所缘,应决定其数目次第。此后应起猛利坚固之心,以自克服,务令如其所预定而修。于此定课不得轻易增减,随时变易,须具足正念正知而修习之。
正行,即主修法门。在《道次第》中,正行部分主要有依止法、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皈依、深信业果、发出离心、发菩提心、止观等,其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观修的内容。
“所谓修道者,即于善所缘,如欲而能令心安住之谓也。”所谓修道,就是将心从不善的所缘中调整出来,令之安住于善的所缘中,通过不断调整练习,达到熟悉安住的效果。
“若于所缘随意修习,依自己所想之数目与次第而修者,从初即养成任意之习惯,将至一世之善行无成,反成有过。”安住于善所缘之后,就应次第而修。如果对所修内容没有固定安排,而是随心所欲,按自己决定的数目和先后秩序进行,从开始就养成任意为之的习惯,将终身难以成就,甚至会使这种错误习惯固定下来,成为障碍修道的过失。
“故最初无论修习何种所缘,应决定其数目次第。”所以在修道之初,无论修习何种所缘,皆应确定数目(修几座)及次第(先后顺序)。因为修行就是正确习惯的养成,这就需要按照一定程序进行。以依止法为例,《道次第》规定每天应修四座,我们就要以此作为常课,并按论中所说持之以恒地观修,才能形成稳定的正念力量。否则,时而修念死无常,时而观三恶道苦,就无法达到所修效果。就像一壶水,刚烧得有几分温热,又换成另一壶,刚有的几分温热又冷却了,怎么可能将水烧开?所以,在修行的数目和次第上必须确定,尤其是对初学者,更要养成这一良好习惯。
“此后应起猛利坚固之心,以自克服,务令如其所预定而修。于此定课不得轻易增减,随时变易,须具足正念正知而修习之。”形成定课后,就要以勇猛精进之心克服障碍,务必按照事先规定的功课修习。对于这些定课,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也不能随意改变,必须具足正知正念而修。良好习惯是修行成就的保证,不能今天心血来潮修五六座,明天又找个借口一座不修,这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问题,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任何一种观修,都是通过思惟善所缘境帮助我们获得正念。对常人来说,一旦遭遇违缘,烦恼便随之而来。而对一个训练有素的修行人,无论面对什么境界,都有能力保有正念。其实,止观并不神秘,世间很多事都需要止和观的参与。比如体育训练,既要将动作调整到位,又要不断练习使之纯熟。其中,调整式的训练就相当于观,而熟悉式的训练就相当于止。《道次第》的修行也是同样,比如修依止法——修观(观察修)时,通过思惟善知识功德生起恭敬心;修止(安住修)时,则令心安住于恭敬中。如果凡夫心现起,就要再观察,再思惟,直到恭敬心再次生起。在反复不断的训练中,这一心行就能逐步稳定并保持良好状态,最终任运自如。
2.修习依止法
先修依止之胜利,及不依止之过患。
次,多起防护,绝不放任,令有寻求师过之心。尽我自己所知师之戒定慧等德,数数思惟,乃至净信未生以来,恒修习之。此后又念于己已作、当作种种利益之恩德,如前所引经说,乃至心中恭敬未生起之间而修习之。
本论略示修法部分,主要是以依止法的修习为例。
“先修依止之胜利,及不依止之过患。”首先,是修习依止的殊胜利益及不依止的过患。其中,依止的利益有八种:一、能得佛位;二、诸佛欢喜;三、一切魔眷不能为害;四、烦恼与恶业自然遮止;五、善缘增长;六、世世不离善知识;七、不堕三恶趣;八、暂时与究竟安乐如愿而得。而不依止和不如法依止的过患也有八种:一、轻师即等于轻佛;二、乱师意而使生嗔恨,如其所乱一刹那,即摧毁一劫善根,得一劫地狱苦;三、不如法依止师者,即修密法殊胜方便,亦不能得悉地;四、不如法依止师,虽依密相续勤习经教,等修地狱因;五、不如法依止,对于功德未生者不生,已生者速灭;六、生病痛不乐意事,常相缠扰;七、后世常流转于无边恶趣;八、生生世世与善知识睽违,不能值遇。时时思惟如法依止及不依止的利弊,才能自觉修习依止法,而不是当做一项任务来完成。
“次,多起防护,绝不放任,令有寻求师过之心。”其次,对凡夫心严加防护,绝不容许丝毫放任,以免对师长生起寻过之心。凡夫总是惯于寻求他人过失,也惯于对得到的一切不加珍惜。对于这两种心行,我们要严加防范,因为这将损减功德法财,正如《永嘉证道歌》所言:“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
“尽我自己所知师之戒定慧等德,数数思惟,乃至净信未生以来,恒修习之。”对于自己所了解的,师长的戒定慧等功德,必须反复思惟。在没有真正生起净信之前,持久不断地加以修习。即使我们目前尚未对师长生起寻过之心,但如果恭敬心不曾圆满,今后也随时可能犯错。防患于未然的方法,便是“净信为本、念恩生敬”。关于这两点,已生恭敬心者也不能忽视。因为任何心念都是缘起的,没有彻底巩固之前,还须通过观修和实践不断滋养。
“此后又念于己已作、当作种种利益之恩德,如前所引经说,乃至心中恭敬未生起之间而修习之。”其后,还要思惟师长对于自己的恩德,包括目前已作的利益,和未来将作的利益,正如之前所引《十法经》、《华严经》等经文所说的那样,在恭敬心不曾真正生起之前,应当以念恩心时时思惟,时时修习。
对于多数学佛者来说,往往既有恭敬心,也有不恭敬心。那么,恭敬心生起后,不恭敬的心理是否会立刻消失呢?其实种子还是在的,只不过变弱了,暂时不起活动而已,但这一潜藏力量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断除。依止法所要做的,正是令恭敬心不断强大,逐渐削弱乃至完全取代不恭敬心,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地修习。
三、结行修法
所积诸善,由《普贤行愿》或以《净愿七十颂》等,于现在究竟诸所应希愿处,以猛利欲乐而回向之。
如是,每日上午、下午、初夜、后夜四次修习。初修之时,如其太久,易为沉掉所扰。若于此串习,将来纠正甚难,故须时间短少,次数增多,稍留余趣,俾引起下次欲修之心。否则将一见座位便生厌呕,必待修习稍熟,乃可渐次延增。于一切所缘,务令不急不缓,离过而修,则障难鲜少,疲劳昏沉等皆能息灭也。
结行,就是修行结束时的回向。无论修加行还是正行,下座前都要将修法功德回施众生,同证菩提。回向可以帮助我们将所修功德固定下来,并指向特定目标。就像电脑处理文件后进行保存那样,否则就会丢失。当然,回向的功能不仅在于保存,以广大愿力进行回向,更可使所修功德增长广大,就像把一个文件同时拷贝为千万份、亿万份,乃至无限。
“所积诸善,由《普贤行愿》或以《净愿七十颂》等,于现在究竟诸所应希愿处,以猛利欲乐而回向之。”《净愿七十颂》,是藏传佛教关于回向的重要经论。对于我们所修的一切善法,下座前,应该依照《普贤行愿》或《净愿七十颂》等经论所说的那样,将现前乃至究竟所希求的种种利益,以勇猛恳切的发心回向法界一切众生。我们的愿力有多大,回向的力量就有多大。如果只是轻飘飘地念过,甚至自己都不懂得念了什么,回向是不会生效的。除了《普贤行愿》或《净愿七十颂》外,常用的回向文还有“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和“愿诸众生常住安乐,无诸病苦,善法坚实成就”等。对于修习依止法来说,则可回向一切有情生生世世得遇善知识。
“如是,每日上午、下午、初夜、后夜四次修习。”依止法,每天应修四次,分别在上午、下午、初夜、后夜。其中,初夜是十八点至二十二点,后夜是二点至六点,这是印度人对时间的区分。
“初修之时,如其太久,易为沉掉所扰。”开始打坐观修时,如果每一座时间太长,很容易被昏沉或掉举所干扰。昏沉,就是其心昏昧,精神不振。有些人可以坐上两三个小时,却是在那里打瞌睡。掉举,就是其心躁动,摇摆不定,以攀缘心追逐境界。这也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过于紧张有关,很多人都像在高速运转中无法停歇的机器,习惯忙个不停。即使下了班,还要用各种娱乐将时间填满。甚至睡觉后仍在东想西想,辗转反侧。久而久之,心就会失去静下来的功能,就像失灵的开关那样,毫无自主能力。这两种是禅修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若于此串习,将来纠正甚难。”一旦在座上养成昏沉或掉举等不良习惯,将来纠正起来会特别困难。其实,打坐并不在于时间长短,关键是保质保量。就像做实验那样,全力以赴将每个步骤做得精确。能按禅修规范坐十分钟,把身体姿势和用心习惯都调整好,才可以延长时间。否则,盲修瞎练,先入为主,很容易将一些错误习惯固定下来。
“故须时间短少,次数增多,稍留余趣,俾引起下次欲修之心。否则将一见座位便生厌呕,必待修习稍熟,乃可渐次延增。”所以,修习应该时间短、次数多,这样就能留有余地,引发下次上座修习的兴趣。否则,很可能一见座位就生起厌倦之心,避之惟恐不及。必须在修行较为纯熟之后,才能逐渐延长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每次禅修时,尽量按计划安排的时间下座,切莫坐到疲惫不堪才结束。那样几次以后,可能就再也不想坐了。如果每次坐得兴趣盎然,才能长久保持修行动力。
“于一切所缘,务令不急不缓,离过而修,则障难鲜少,疲劳昏沉等皆能息灭也。”急,是对所缘过分着意,容易造成紧张和疲劳,不易持久。缓,则是观修中用力不足,心无法专注。对于观修的一切所缘境,应该不急不缓。远离过急和过缓两种过失,修道障碍将大大减少,同时也能断除疲劳、昏沉等过失。
修习止观,就是通过观察修的调整和安住修的安住来熟悉这一心行状态。在观修所缘尚未清晰时,应该多多用心。一旦调整到位,就不必太过用力,安住即可。如果调整过度,反而不易得定。初修时,安住时间可能很短,待所缘模糊之后,就要再次以观察修调整。这个过程虽不玄妙,但其中很多细节需要精确。何时用心,用到什么程度,都要恰如其分。具体问题,必须由具有止观经验的师长进行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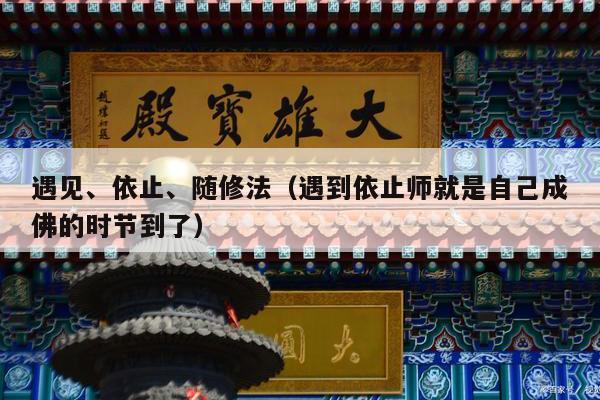
听僧人讲,如何鉴别是正法还是外道?
自己正,才能鉴别别人是正是邪。
-----
佛说演道俗业经
乞伏秦沙门释圣坚译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菩萨无数。四辈之众。天龙鬼神阿须伦会。
时给孤独氏与五百居士。出舍卫城行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叉手问佛。居处治家财有几辈。出家修道行异同乎。当奉何法疾成无上正真之道。复以何宜化众生耶。
佛言。善哉问也。开发曈曚将来学施。
佛言。财有三辈。一曰下财。二曰中财。三曰上财。
何谓下财。有人治产积聚钱财。不敢衣食不修经戒。不能孝顺供养二亲。不乐随时给足妻子。欲其消息充饶饱赐。奴客徒使衣裁蔽形食系口腹。抱愚守惜如蜂爱蜜。不信先圣不奉高士沙门道人。不好布施种福为德。心自计常不虑对至。合者必散祸福自追。贪慕身地不觉恼恨。咄嗟没过入泥黎门。其身缘食四大虺盛。神寄其中假号为名。羸弱犹化危脆不固。不解非常倚世之荣。心怀万忧谓亦长生。心存吾我不达悉空。三界尚虚况人物乎。汲汲迭惑贪淫嫉妒。如斯行者。
奉养父母安和至心。出辞还返不失颜色晨定暮省小心翼翼。念二亲恩而无穷极。给足妻子应时衣食。恩情归流与共同欢。妻子如是也终无私行。瞻视奴客眷属徒使不令饥乏。不信死后当复更生。谓死灭尽归于无形。供孝所生念乳养恩。给足妻子恋恩爱情。瞻视仆使欲得其力。不能奉敬沙门道人。不肯行善布恩施德。后当得福与众殊特。是谓中财。佛于是颂曰
常能念乳养 孝顺供二亲
给足其妻子 随时不失节
奴客及徒使 慰劳不加恶
下侍皆顺从 遣行不违教
不信后世生 闻之惊不喜
自计身有常 长存不终亡
三界如幻化 当识此辞章
己所为罪福 从本而受之
佛复告长者。上财业者。谓其人若有财宝能自衣食。孝顺父母不失时节。恒瞻颜色不令怀戚。出不犯禁入不违礼。造行清白不使污染。恭敬尊长谦逊智者。启受博闻等心不邪。下劣贫厄咸蒙仗荷。给赡妻子常令备丰。除诸邪念修以正治。消息奴使不令穷匮。不妄挝骂加之慈愍。奉敬先圣至学正士出家顺法沙门贤明。夙夜行礼不失其意。布施所乏使成道德。恣讲经典并化痴冥。以善方便不失其时。自安护彼一切众生。犹如牸牛食刍出乳。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醍醐最柔特妙。其自安身愍哀十方。多所慈念多所安隐。诸天人民皆得蒙度。是人最尊无上无比为无俦匹为世大雄独步无侣。佛于是颂曰
若有众财业 以自好衣食
供养孝父母 不失其颜色
出游不犯禁 还返不违礼
造行常清白 顺法不荒迷
供敬奉尊长 谦逊明智者
启受博闻士 等心不慕邪
随时给妻子 各令得其所
慈赐奴仆使 衣食常丰足
奉沙门学士 布施授供养
从受深妙法 弃捐痴聋盲
愍伤十方人 不独为身行
常自安其已 亦解一切厄
譬如酥醍醐 本从刍草出
既可用安身 身和无疾疹
普哀众生类 其心常平一
以是四等行 速逮成至佛
佛告长者。出家修道学有三品。一曰声闻。二曰缘觉。三曰大乘。
何谓声闻。畏苦厌身。思无央数生死之难周旋之患视身如怨。四大犹虺五阴处贼。坐禅数息安般守意。观身恶露不净之形。畏色欲本痛想行识。怖地狱苦。饿鬼之厄。畜生恼结。人中之难。天上别离。不可称计。轮转无休如狱中囚。欲断生死勤劳之罪。求无为乐泥洹之安。但自为己不念众生。常执小慈不兴大哀。倚于音声不解空慧。三界犹幻。趣自济己不顾恩慈。是为声闻学。佛于是颂曰
畏无量生死 周旋之艰难
心已怀恐惧 唯欲求自安
坐禅而数息 专精志安般
观身中恶露 不净有若干
弃捐三界色 断欲得自安
不能修大慈 唯志乐泥洹
佛告长者。缘觉者。本发大意。为菩萨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以用望想求为尊豪天上天下咸令自归。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威神德重巍巍堂堂无能及者。不解如来色身所现。因世愚人不识大道。断生死流不能反原。尽生死本故为现身。相好严容。文辞言教以化愚冥。显示大明及著相好。谓审有色像。虽行四等四恩六度无极三十七品。观十二缘欲拔其原。不解本无悕望大道。正使积德如虚空界不得至佛。所以者何。用不达故。何谓不达。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四等四恩有所悕望。念救一切五趣生死。解空无想不愿诸法。晓一切法如幻化梦野马影响芭蕉泡沫皆无所有。道慧无形等如虚空。无所增坏普度众生。佛于是颂曰
本发菩萨意 志慕大乘业
但欲著佛身 不了无适莫
布施戒忍辱 精进禅息智
四等恩六度 惟己乐无为
慕三十二相 八十好巍巍
天上天下尊 脱五阴六衰
但察其粗事 不能观深微
虽欲度十方 心口自相违
不了如幻化 水沫泡野马
芭蕉如梦影 妄想甚众多
正使作功德 犹如江河沙
心怀无上真 不解除众魔
佛告长者。其大乘学。发无上正真道意。行于大慈等如虚空。而修大悲无所适莫。不自忧身但念五趣。一切众生普欲使安。奉四等心慈悲喜护。惠施仁爱益义等利救济十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六度无极无所悕望。以施一切众生之类。观于三界往返周旋。勤苦艰难不可称计。念之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而无异。为之雨泪。欲令度厄至于大道。佛于是颂曰
发无上大意 行慈悲喜护
大哀如虚空 行等无适莫
立德不为己 唯为十方施
度脱诸群生 使至大道智
又有四事得至大乘。
一曰 布施给诸穷乏。
二曰 不择豪劣行轻重心。
三曰 所可施与无所悕望不求还报。
四曰 以此功德施于众生。
佛于是颂曰
布施摄贫穷 不行轻重心
志慧无悕望 不求还得报
愍念于群黎 往来周旋者
以此功德施 悉令至大道
佛告长者。奉戒有四事疾成大乘。
一曰 守口护身心不念非。
二曰 出入行步不失礼节。
三曰 不愿生天转轮圣王释梵之位。
四曰 以是禁戒惠施众生。
佛于是颂曰
常护身口意 心坚如太山
若出入行步 未曾失礼节
不愿生天上 释梵转轮王
则以此正行 用惠一切人
佛告长者。忍辱有四事疾成大乘。
一曰 若骂詈者不计音声。
二曰 若挝捶者计如无形。
三曰 若毁辱者谓如风吹。
四曰 有加害者常怀大哀。
佛于是颂曰
挝骂令默然 自计本无形
设有恨意起 心辄还自止
和心颜色悦 众人咸恭敬
用是得成佛 三十二相明
佛告长者。精进有四事。
一曰 夙夜奉法未曾懈废。
二曰 宁失身命不违道教。
三曰 勤讽深典不以懈惓。
四曰 广欲救济诸危厄者。
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夙夜奉大法 未曾有忽忘
宁自失身命 不敢违道教
诵习深经典 不以为懈惓
救济众危厄 不使心怀怨
佛告长者。禅思有四事。
一曰 乐习精修闲居独处。
二曰 静身口心令不愦乱。
三曰 虽在众闹常能定己。
四曰 其心旷然而无所著。
佛于是颂曰
恒好于精修 志闲居独处
静其身口意 未曾念愦闹
数处众乱中 心定无忽变
一心见十方 道慧起神足
佛告长者。智慧有四事。
一曰 解于身空。四大合成散坏本无主名。
二曰 其生三界皆心所为。心如幻化倚立众形。
三曰 了知五阴本无处所。随其所著因有斯情。
四曰 晓十二缘本无根原因对而对现。
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悉解其身空 四大而合成
散灭无处所 从心而得生
五阴本无根 所著以为名
十二缘无端 了此至大安
佛告长者。智慧复有六事。
一曰 解色如聚沫。
二曰 了痛痒如水泡。
三曰 思想如野马。
四曰 晓生死如芭蕉。
五曰 察识如幻。
六曰 心神如影响计本悉空皆无处所。
佛于是颂曰
解色如聚沫 痛痒如水泡
思想犹野马 生死若芭蕉
了识假譬幻 三界无一好
分别悉空无 尔乃至大道
佛告长者。慈有四事。
一曰 慈念十方。
二曰 如母育子。
三曰 极愍念之。
四曰 如身无异。
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慈念于十方 如母育赤子
常怀极愍念 如身等无异
佛告长者。哀有四事。
一曰 愍之。
二曰 为之雨泪。
三曰 身欲代罪。
四曰 以命济之。
喜有四事。
一曰 和颜。
二曰 善言。
三曰 说经。
四曰 解义。
护有四事。
一曰 教去恶就善。
二曰 常训诲归命三宝。
三曰 使发道意。
四曰 开化众生。
是为四。
佛于是颂曰
愍念为雨泪 身欲代其罪
舍命而济之 不以为怀恨
和颜演善言 讲法分别义
教去恶就善 诲归命三宝
佛告长者。有四法疾。成无上正真之道。
一曰 解空学无所求。
二曰 无想无所悕望。
三曰 无愿不慕所生。
四曰 常等三乘之业无去来今。
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解空无所求 无想悕望报
不慕愿所生 常等三世行
佛告长者。有四事法疾成佛道。
一曰 一切皆悉本净。
二曰 而解万物普如幻化。
三曰 生死断灭皆从缘对。
四曰 计其缘对本亦无形。
佛于是颂曰
一切悉本净 解物如幻化
生死从缘对 计本亦无形
佛告长者。有六法疾成正觉。
一曰 身常行慈无怨无结。
二曰 口常行慈演深慧义。
三者 心慈仁和调隐哀念十方。
四曰 护戒不造想求大乘之业。
五曰 正观见十方空道俗不二。
六曰 供足乏食救身之业以济危厄。
是为六。佛于是颂曰
身常行慈心 未曾捶怨结
口恒修言愍 演深慧之谊
心和仁调隐 哀念诸十方
护戒不起想 正观十方空
佛告长者。有四事疾成佛道。
一曰 奉精进业悉无所著。
二曰 教化众生道心不断。
三曰 游于生死不以患厌。
四曰 大慈大哀不舍权慧。
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精进无所著 教化未曾断
不患厌生死 不废舍权慧
佛告长者。开化众生有四事。
一曰 不信生死者则以现事祸福喻之。
二曰 不信三宝显示大道。
三曰 迷惑邪径指语三乘。佛道独尊而无有侣。
四曰 三界所有悉如幻化无一真谛。
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不信生死祸福示 堕邪见者显大道
佛道独尊而无侣 三界悉空如幻化
佛告长者。开化复有七事。
一曰 悭贪者教令布施。
二曰 犯恶者诲令奉戒。
三曰 嗔恚者劝令忍辱。
四曰 懈怠者化令精进。
五曰 心乱者诲令定意。
六曰 愚冥者教令至学智度无极。
七曰 不知随时显权方便。
是为七。佛于是颂曰
悭者教布施 犯恶令奉戒
嗔恚劝忍辱 懈怠劝精进
乱者使定意 愚冥教令学
智慧度无极 随时发善权
随时菩萨问佛。何故学者有上中下。不悉普等至大乘乎。
佛言。学者其心见有远近 解有深浅 志有优劣 故示三乘。计本无三假引为喻。譬如有人为国大臣聪明智慧。王之所重参谊国事。一以委托不怀疑虑。又斯大臣有三亲友。一曰太子。二曰尊者。三曰凡人。大臣举治国之政颇有漏失。众人潜入白之于王。谓图逆辟王闻怀疑问诸臣曰。当何罪之诸臣得便各重罪之。或言斫头。或言截手断足或言割耳及鼻。挑眼去舌。王察众臣所议甚重。告曰不然。此人明达偶有小失。不宜乃尔当捉闭著狱。诸臣唯从不敢复言。告边臣曰。速下文书令收敕臣闭在刑狱。时凡亲友闻之悲念。欲使出狱力劣不任。唯以衣被饮食所乏日日供之。亦不能令不见考治。尊者又闻心用辛酸。往至其所解喻狱吏。不令搒笞痛苦休息不堪出狱。至太子闻以为罔然。是吾亲亲无有重罪。众臣憎之谗之于王。不宜取尔。往诣王所具陈本末谓无逆肆。当用我故愿赦其殃。王用爱子即赦使出狱。与王相见令业如故。其国王者谓如来。其太子者智慧度无极善权方便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权慧之宜。乃能得出于三界狱。得成为佛广济众生。尊者亲友谓行净戒。免三恶趣不助三界。可受天上人间福不得至道。凡知友者。谓布施业。此适能脱饿鬼之界。不免地狱畜生之厄。所以者何。如其所种各得其类。发无上正真道意。奉于大慈无极大哀。开化一切故得至佛道。本典大道不达深法。不解进退中止自废。故为缘觉畏生死难往返周旋。但欲自济不念苦人故堕声闻。各随本行而获致之。
说是经时。给孤独氏居士五百长者。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有数千人远尘离垢诸法眼生。箜篌乐器不鼓自鸣。飞鸟走兽相和悲声。当是之时。莫不欢喜自归佛者。
居士复问。初学道者始以何志。
佛言。先习五戒自归于三。
何谓五戒。
一曰 慈心恩仁不杀。
二曰 清廉节用不盗。
三者 贞良鲜洁不染。
四曰 笃信性和不欺。
五曰 要达志明不乱。
何谓三自归。
一曰 归佛无上正真。
二曰 归法以自御心。
三曰 归众圣众之中所受广大。犹如大海靡所不包。
复有四法。一曰道迹。二曰往还。三曰不还。四曰无著。缘觉至佛无上大道。得天人身皆由之生。次行四等四恩四辩六度无极大慈大哀得成大道。前知无穷却睹无极。教训十方何智不逮。
阿难问曰。此经何名。云何奉行。
佛言名曰解俗家。业三品之财出家修道无上正真。其要号曰演道俗业。
佛说如是。贤者阿难。给孤独居士。五百清信士。莫不欢喜。
无相心三昧(无想心三昧)vipassana 观禅
无相心三昧(无想心三昧)vipassana 观禅
(界定法师)最后浅说一下无相心三昧。
有的人说原始经典中的无相心三昧,与大乘佛教的“空”观思想十分接近。我本人比较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二者还是有所区别。作为一种修持法门,它总有一个对治的对象,比说空是对治有,苦是对治乐,等等。相既是实在物(山水自然景观人物),也可以是虚幻之物(念头、梦想、意识)。我们平常人喜欢“取相”,结果我们的脑海中,为各种各样的“相”所充斥。“相”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可是执迷于相,就会很麻烦。如此时间久了,我们的思想就变得复杂了,种种烦忧就此而生起,故而“相”便成“相患”,以相为患。
取相是想蕴认知一切事物的作用,而这个相,又往往是颠倒的,不真实的,因而《金刚经》中的破四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对治我们的种种不净之想,以清净想来取代不净之想、染杂之想。无相心三昧,便是建立在破四相基础之上的一种修禅对治法门。修行此禅定法门,其次第大致分为八个,即村邑想、同修梵行想、森林独处想、大地想、空无边处想、识无边处想、无所有处想、非想非非想处想。每一个次第都是后一想取代前一想,一个一个地见味、见患、见离。不仅如此,还要观照一切法唯是名言,无有实性(假名无实故)。如此一来,即于法不起所缘想,进而能缘心想也不可得,能所空性无所对立,见性绝对,由此而入无相心三昧。
(阿含辞典)无想心三昧:
另作「无想心定;无想定」,南传作「无相心定」(animittaṃ cetosamādhiṃ),菩提比丘长老英译为「无标记之心的集中贯注」(the markless mental concentration, AN),或「心之无形迹的集中贯注」(the signless concentration of mind, SN/MN)。《显扬真义》说,这是关於舍断常相等后,被转起的毘婆舍那定(vipassanāsamādhiṃyeva, SN.40.9); 无相定是一种毘婆舍那定vipassana ,以常相等的根除(niccanimittādīnaṃ samugghātanena, SN.22.80)被称为无相,《破斥犹豫》以「毘婆舍那心定」(vipassanācittasamādhiṃ, MN.121)解说,《满足希求》说,无相是强力的毘婆舍那定(balavavipassanāsamādhiṃ, AN.7.56)。
无相心三昧:
另作「无相心正受」,南传作「无相心解脱」(animittā cetovimutti),菩提比丘长老英译为「无标记的心释放」(the markless liberation of the mind, AN),或「无形迹的心的释放」(the signless liberation of mind, SN)。《显扬真义》说,这是13法:毘婆舍那(除去常相、乐相、我相)、四无色[定](色相不存在)、四道与四果(以相的作者之杂染(nimittakarānaṃ kilesānaṃ)不存在, SN.41.7)。又,依《相应部41相应7经》、《中部43经》,进入后住於「无相心定」被称为「无相心解脱」,依《杂阿含567经》, 「无想心三昧」即「无相三昧」 ,依《杂阿含272经》与《相应部22相应80经》的比对,「无相三昧」即「无相定」的另译,依《中阿含211经》与《中部43经》的比对。「无想定」即「无相心解脱」等至。
我们培育定力为了什么?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培育定力有很多种功德,有五种功德。例如:现法乐住、vipassana观禅、神通、灭尽定和胜生(就是投生到梵天界)。
我想问问大家, 培育定力(止禅)的目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五种功德的第二种vipassana,为了修观。
修观(vipassana观禅)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提升智慧。 所以佛陀教导修定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提升智慧,而不是让我们只是安住于定境去享乐,并不是这个目的。也不是让我们培育定力去开发神通,也不是让我们培育定力去为了投生到梵天界,这也就是一个人修习世间定和修习出世间定的差别。
对于修定的外道来说,他们修定的目的是为了投生到梵天界,或者他们为了内心享受很殊胜、很寂静的快乐。但是佛陀教导修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的解脱。
曾经有位洋人的尊者,他问我说:“外道也修定,那为什么要把定称为觉支呢?”大家请回答,为什么?外道也修定,既然外道也修定,那为什么又要把定称为觉支?觉支是什么意思?bojjhanga或者完整地称为sambojjhanga,sambojjhanga它的意思是sambodhi再加上anga,sambodhi是什么意思?sambodhi是正觉,anga是因素、条件。
导向正觉的条件、因素,称为觉支。既然这么样,外道修定也可以导向觉悟了?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外道修定并不是导向涅槃,它并不是导向修观智而最终导向涅槃,它是为修定而修定,我们是为修慧而修定,这个是差别,这是外道定和佛陀教导的定的差别。所以外道修定不能称为定觉支。
即使作为佛陀的弟子,如果你修定是为了投生到某些地方,例如:你修定是为了投生到梵天界,你的定力、你的三昧仍然不能称为定觉支。因为它只能够延长你的轮回,所以这种定不能够称为正定。
佛陀教导“阿毗达摩”,最终是要让我们断除一切烦恼,让我们灭尽一切诸苦。要如何才能够断除一切烦恼呢?要断烦恼唯有通过道智,也就是圣道才能断烦恼;要断除烦恼必须得要修行,必须得修vipassana(观禅),维巴沙那(毗婆舍那)。要修观,培育观智。 什么是观呢?观就是观照一切名法跟色法的无常、苦、无我。 “阿毗达摩”所分析的无外乎是心法、心所法、色法。但是,所有这些心法、心所法、色法,都是属于行法、有为法,它的本质是无常、苦、无我的。佛陀教导“阿毗达摩”并不是只是让我们去明白、去了解,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去观照它,然后再去超越它。就象佛陀把贼指出来之后,还教我们如何把贼抓起来。怎么抓贼呢?要用智慧的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所以,“阿毗达摩”的目的是教导我们要修观,修观的目的是为了断除烦恼。所以,我们学习“阿毗达摩”就有这样的意义。
(玛欣德尊者 阿毗达摩)
【禅修业处的指导】
止禅
世尊通过指导修行止禅,平息人们散乱、疯狂的心。止禅(samatha)的修习是以平等及正思惟,将心安住于单一目标,使散乱的心得以调伏。凡夫未受训练的心,从无始轮回以来即四处飘荡,若不用正念之绳将其拴在禅修的业处上,如呼吸(入出息念)等,便很容易走向邪恶,因为这是心的倾向。正如《法句》第十一经所说:「心乐于恶法」。佛陀教导四十种禅修的业处如,入出息念、白骨观(aññhika-sa¤¤à)、四界分别观、三十二身分、白遍等,以此平息及调伏众生纷乱扰动的心。
我们应知道,佛陀佛陀教导各种不同的业处是为了适应众生不同的性格(carita)。如对贪根比较重的众生,世尊便教导他们修习十种死尸腐烂的「不净观」,或观察自己的身体由三十二不净的部分,如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肉、腱、骨等组成的「三十二身分」,作此观能协助众生克服对自己及他人色身的贪欲。
至于对瞋根较重的众生,佛陀教导他们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是希望一切众生幸福、快乐;「悲」是在看到他人遭受痛苦时心生不忍,希望拔除别人的痛苦;「喜」是随喜他人的成就与富裕;「舍」是以智慧了解业是一切众生的主人或遗产,众生的得失、苦乐都与业相关。由修「四无量心观禅」能产生不执著、平等对待他人的心境。
对于痴根重及心散漫的众生,「安般念」(入出息念)是最理想的业处。而对于信心强的众生,世尊便指导他们观想或随念佛(佛随念)、法、僧的德行;或教导「舍随念」,以忆念自己慷慨大方布施的功德,激发起欢喜心,进而由欢喜而生轻安,从轻安而得定。对于慧根强的众生,则适合观生命之无常,死亡随时随刻发生的「死随念」,或分别色身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四界分别观」(界差别观)。
当一切烦躁扰动的心通过心一境性(ekaggatà),向单一目标进发而得以安止,它就会变得集中、轻快、柔软、易操作、清澈及宁静。有定的心就能如实知见五蕴或名色的真实本质。正如世尊在《相应部•蕴品•三摩地经》(Samàdhisuttaü, S.III.I.i.5)中所开示:「比丘!你们应当培养定力,有定力的比丘能够如实知见诸法。何谓诸法的实相?那是五蕴的生与灭。」因此,在修行的道路上,定的培育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观禅 vipassana
在定的基础上,佛陀教导能受教的众生修观或分析五蕴(名色),辨认所谓的「人」或「我」只是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之下所生起的「五蕴法之组合」,除了色、受、想、行、识,在这之内或之外,并没有一个真正能主宰的「我」存在。这是「名色分别智」(nàmaråpa-pariccheda-¤àõa)。
【此故彼之因缘法】
紧接着,世尊继续让禅修者探索五蕴法生起的因缘。今世五蕴之果报身不是无端生起,也非万能之神所造,而是因为过去世的无明、爱、取、行及业五个因造成的;如果烦恼不断,今世的无明、爱、取、行与业将产生未来的五蕴果报身。
在十二缘起(pañiccasamuppàda)支中,过去的无明、爱、取构成「烦恼轮」(kilesavañña);行与业构成「业轮」(kammavañña),今世的五蕴或识、名色、六入、触与受构成「果报轮」(vipàkavañña)。因为对四圣谛及因果的无明,以及贪爱五官的享受和生命的持续,人们因此造善与恶之行业;一旦所造之业成熟,人们将随业投生于相关的生存地;再加上烦恼的缘故(烦恼轮),人们又继续造作(业轮),导致下一世的投生(果报轮)。这三轮就这样不断地持续轮转下去。
了解世间的一切为因缘法——此生故彼生;缘于无明,行生起;缘于行,识生起;缘于识,名色生起……。了解此灭故彼灭;因为无明灭,所以行灭;因为行灭,所以识灭;因为识灭,所以名色灭……。因此禅修者越度了关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疑惑。能够辩识因果互相牵引的能力,即称为「缘摄受智」(paccayapariggaha ¤àõa)。
随后,佛陀继续教导禅修者以正思惟来辩认五蕴——「这不是我的」(苦随观)、「这不是我」(无常随观)、「不是我的自我」(无我随观)。五蕴或名色的不断生灭是「无常」;不断受生灭压迫是「苦」;不能受到控制,为因缘所生,没有一个永恒的实体是「无我」。无论是过去世、现在世或未来世,内在与外在的所有名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当一再地观名色的无常、苦、无我时,观智将变得敏锐,禅修者便不再注意名色的“生起”,而只见到它们不断地“消失”与“坏灭”。禅修者对这些不断坏灭的名色法生起「怖畏」,觉知一切行法都是不圆满的、充满过患,于是开始对它们感到「厌离」。
正如用竹篓抓鱼的渔夫,习惯地将手伸进篓口中,以探知鱼儿是否入篓;如果手碰到鱼儿,渔夫便会高兴地从篓中将鱼儿取出。这次,当他的手碰到滑溜的物体时,便如往常般地从篓中将它抓出,在看到所抓的动物颈项有三条斑纹时,他便知道这是有危险、极毒的水蛇,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被反咬一口,有可能会被置于死地;渔夫因此不再感到高兴,反而害怕极了。他对这毒蛇感到厌恶,他很想摆脱它;因此他抓紧水蛇,在其头上打旋三次,并用最大的力气把它丢到最远的地方,然后赶紧跑到高地去;唯有这样,他才会觉得安全与自在。
同样地,当禅修者发现所执著、热爱的名色原来是充满过患的(无常、苦、无我),他们便会感到厌离、只想摆脱,就像欲摆脱毒蛇的渔夫。为了要摆脱名色的纠缠,禅修者除了继续观名色的无常、苦、无我三相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为。正如欲摆脱危险的渔夫,不敢随便就放开毒蛇,因为它很可能转过头来咬伤自己;因此,唯有将其削弱至无力伤人之后,再把它丢弃远处。
当禅修者再观名色的无常、苦、无我的真相时,常、乐、我的假象便会相对地转弱。此时,当禅修者继续观照名色的三相时,他便会逐渐舍弃怖畏与欲乐,并对一切行法感到中舍,这是「行舍智」(saïkhàrupekkhà ¤àõa)。当行舍智的智慧成熟时,禅修者便能见到涅槃——在他心中生起了于无始轮回中从未生起过的须陀洹(入流)道心,此道心取涅槃为终极目标;它同时彻知苦谛、断除集谛,证悟灭谛及开展道谛。如果禅修者有足够的波罗蜜,继续精进修行,他则可以证得「阿罗汉道果」,并从烦恼中得到永恒的解脱。这是佛陀如何逐步地引导众生,使他们了解所谓的「永恒身心」及执取,原来是那么的不可依靠,并因此自愿地舍离爱欲。(善戒尼师 阿毗达摩)
止观,止为梵语 śamatha (止禅 奢摩他),
观为梵语vi-paśyanā (观禅 毘婆舍那vipassana)之译;
止息一切外境与妄念,而贯注于特定之对象(止禅 奢摩他),并生起正智能以观此一对象(观禅vipassana),称为止观, 止与观相辅相成以完成解脱道,彼此有不可互离之关系,一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圆满完成解脱之阿罗汉者,是依着止观之方法多所作与勤修习,截断烦恼与疏远随眠,其方法可依四种修习法或随其中一种方法,达成截断烦恼与疏远随眠,终至圆满解脱之阿罗汉。
( 一 ) 依止修观:于欲贪染与寻思麤重者,先由不净观与数息观,平息身心之麤动而渐次修观,此依止修观法为最为普遍之修习法。
( 二 ) 依观修止:于法善观与薄尘者,观察五蕴、六处之集、灭、味、患、出离如实作观,使身心沉淀止息,而渐次相应于止。
( 三 ) 止与观一双统修:止能增上观;观亦能增上止,止与观交互修习增上,而达于止观平衡之统合修习,前二之修止观法,如果相互淳熟后亦能达此止与观一双统修。
( 四 ) 意离于法之掉举:此一方法为禅定 ( 止 ) 不深厚,但意志力坚强坚固,远离对五蕴、六入处法之掉举,安住正持而专注一趣,此为须深盗法中未有四禅八定之慧解脱阿罗汉所修习。
由上四支止观修习法,不论是谁,明示得阿罗汉者,悉是由此等四支,或其随一,皆能成就解脱生死轮回之无生者。
南传增支部二 行品 263-264)
北传杂阿含二一(大正藏、二‧一六 c)
「友!比丘或比丘尼不论谁,凡于我前,明示得阿罗汉者,悉是四支,或由其随一。四者为何?
友!世间有比丘,依止修观,于依止修观彼道生,彼习其道,多所作,彼习修、其道,以多所作结断,疏远随眠。
复次,友!有比丘,依观修止,于依观修止彼道生,彼习其道,多所作,彼习修、其道,以多所作结断,疏远随眠。
复次,友!有比丘,止与观一双统修,止与观一双统修彼道生,彼习其道,多所作,彼习修、其道,以多所作结断,疏远随眠。
复次,友!比丘意离于法之掉举,彼坚持。友!彼安住正内、正止、趣一境、正持时,彼之道生,彼习此道……疏远。
友!比丘或比丘尼,不论是谁,凡于我前,明示得阿罗汉者,悉由此等四支,或其随一。」
(三十七道品 ──向灭比丘 著Sotāpannaka-bhikkhu)

本文链接:https://www.sjxfo.com/bk/xuefo/3290.html
转载声明:本站发布文章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