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性由的简单介绍

佛教中所说的我们每个人的自性真如是如何得来的?
富楼那尊者曾向释迦穆尼佛问过这个问题。佛的回答记载于楞严经卷四。是好问题也是很难的问题,作为后辈,我们应当依法不依人。有问题经中都有解答。
而我浅陋的理解是:自性迷失就是染污,而迷失者在迷失之前不会料到自己会迷失。即原本为佛,迷而苦恼如今。而修炼像是仙家,佛教修行。就是修改行为,正体现一种回归。信佛者是在回归,而不是追求一种新的境界。而是放下许多陋习和沾染,回归。
依法不依人,佛经若读的通透,自能解人我之疑问。自利利他,祝您成就
佛教为什么不提倡杀生
一、关于戒杀
(一)戒杀的必要性
在十不善中,有两种不善的罪业是最为严重的,一个是杀生,另一个是邪见。
为什么杀生的罪业有那么严重呢?首先因为杀生对其他生命构成了极大的伤害;其次从自己的角度而言,杀生的严重果报是惨堕地狱,所以将杀生的罪业排在了第一。
为什么邪见的罪业有那么严重呢?唯识宗认为,在众生的阿赖耶识中,储藏了许多善恶的种子。一旦我们的心里生起了邪见,这些邪见就会摧毁所有善法种子的力量,从此以后,相续中的所有善种或者善根都会因此而间断。
平时所说的邪见,不一定属于十不善中的邪见。十不善中的邪见是什么呢?《俱舍论》中讲过,就是认为不存在善恶因果,不存在前后世之类的观点。因此,从破坏善根的角度来说,十不善中最可怕的就是邪见。
今天在这里,我们暂时不强调邪见,而只以戒杀放生为主题。
为什么要戒杀呢?要想意识到戒杀的重要性,就需要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来进行换位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这样思维:每个人在来到世上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地去寻找自己的理想、追求与爱好。比如说,有些人因为贪图钱财,而愿将体力、青春,以及千载难逢的人间岁月等所有的一切,都花费在追逐金钱的“事业”之中;有些人因为崇尚地位,为了赢得高官厚爵,宁可舍弃包括辛苦换来的钱财在内的所有一切;另有一些人却垂青于名声,为了名满天下、流芳百世,又置钱财、地位于不顾。尽管每种人都各有图谋,但愿意为了金钱、地位与名声而付出生命的情况却异常罕见。由此可见,对于所有人来说,生命的价值都是极其珍贵的,一切世间万法均无法与之比肩。
但很奇怪的是,虽然人类万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却将其它众生的生命视若草芥。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会亲自动手去杀害这些众生;即使自己不动手,也会在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或者在为了获取利润的情况下,眼见他人灭绝人性地残杀这些无辜生命,却熟视无睹、冷眼旁观,不愿尽己所能地规劝阻拦。
我们自以为人类文明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但由人类发明的残酷杀害、虐待其他生命的方法,却在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层出不穷。这些现象除了能证明人类的愚蠢、无知、贪婪与野蛮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吗?既然人类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怎能随意剥夺他众的生命呢?
人类不仅肆无忌惮地屠杀无辜生灵,还为自己的恶劣行径寻找了一些所谓的正当“理由”与“依据”。
基督教以及释迦佛住世时的一些婆罗门的宗教认为:动物是上帝等神灵赐给人类的食物,以动物为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外,很多人都知道,二元论的缔造者笛卡儿甚至认为:动物只不过是一种自动的机器,是没有任何感觉的物体。自从他创立了这种学说之后,西方医学界就开始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残忍地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使无数生命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凌虐。
本来依照常规,在各个宗教、各种学术之间,大家都应当互相尊重、和平共处,而不应该以严厉的态度去驳斥对方。但上述观点不但导致了自己观念上的错误,而且还对其它众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我们就必须毫不留情地给予破斥。
首先,认为上帝等神灵将动物赐给人类为食的观点,是绝对无法证明的。时至今日,上帝存在之说已经成为令西方人深感头痛的一种尴尬,虽然无数人都在绞尽脑汁地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但至今尚一无所获。
当然,我们并不是想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既然上帝存在之说尚是一个悬案,那么所谓“上帝”将动物赐给人类为食的观点又如何以理服人呢?
至于笛卡儿的观点就更是不堪一击,包括小孩子都知道,像黑猩猩之类的很多动物,其智力、情感都跟人类不相上下。如果认为动物没有苦乐感受,就真是可笑荒唐了。因此,这两种说法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荒谬之说。
既然动物也跟人类一样具有知性与感受,不愿意承受痛苦的折磨,那么人类究竟该如何对待动物呢?关于这个问题,世间人以前并没有拿出明确的答案,后来在近几百年间,西方才开始制定了一些善待动物的法律条文,以约束世人日益疯狂的残暴行为,但这些条例所规定的范围,却是极其狭窄的。哲学与其他宗教,也没有在此问题上给出完整的答案。而世人奉为圭臬的科学,又根本无法以自己的结论唤醒人们的良知,建立起伦理道德的观念。唯一能够全面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释迦牟尼佛的经典。
(二)戒杀的三种层次
佛在小乘的经典当中,提出了戒杀的三种层次:
第一种,是最低的要求。就是如果做不到发誓不杀害所有生命,就可以在动物当中进行选择,比如不杀猪、鸟、鱼、羊或者牛等等;或者发誓除了鱼类之外,不杀害其它的所有生命;或者发誓除了在生病的时候,为了治疗疾病,而杀死体内的寄生虫之外,绝不杀害其它的所有生命;或者发誓不杀害现在不太可能杀害的老虎、大象、熊猫等等珍稀动物,包括发誓不杀害现在根本不存在的恐龙,也有一定功德。虽然这是一种不完整的戒杀,也比完全不戒杀要稍强一筹;
第二种,是中等的要求。就是只有当遇到命难时才杀生,比如在肺、肝等器官中发现了寄生虫,如果不打死,自己就会死亡,为了保住性命,才不得已而杀之;或者在仅剩的少量食物中发现了虫子,如果自己不吃完这些食物,就肯定会饿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赶走小虫,独吞该食,除此之外,绝不杀害任何生命;
第三种,是上等的要求。就是无论遇到何等的困难,也绝不杀死任何生命。仍以前面所说的情况为例。
如果在身体内发现了蛔虫之类的寄生虫,要治疗疾病,就必须将其打死,不然自己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细菌是否属于众生,至今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答案,所以这里暂时将细菌排除在外。
另外,在仅剩的食物中发现了虫子,如果将这些虫放到其它地方,它们就会因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而必死无疑;若将仅有的食物布施给虫子,自己又将命丧黄泉。在不是将虫子扔到一边,就是要放弃自己生命,二者不可两全之际,若有纵然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绝不故意伤害其它众生的决心,就算是最崇高的发誓。
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在西藏动乱期间,曾涌现过很多这方面的公案:
有一位上师,在有人将四肢被捆绑的牛、羊等动物放在他的面前,又将屠刀交给他,强迫他去杀害这些生命的时候,曾大义凛然地将屠刀对准了自己的脖子,甘愿以死来捍卫自己的誓言,也绝不向残害众生的邪恶势力低头;
在“除四害”的年代,一位在监狱服刑的出家人,从管教干部处得知了第二天将要捕杀麻雀的计划后,就偷偷去厕所,用小刀割断了自己的血管。旁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
前几年有一个小出家人,他因为病得苦不堪言而到医院去治疗,结果发现折磨他的病因,是腹腔内的大肠已经腐烂坏死。只有杀死一条狗,并用狗的大肠来替换他自己的大肠,才能把病治好。当他知道后,便急切地告诉周围的人:千万不能为了自己的病,而杀死狗的性命,宁死也不肯接受这种治疗方案。他的上师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开心,并赞不绝口地说道:“学佛的人就是应该这样!学佛的人就是应该这样!!”
这些都是真实的事例,前面两个公案中的其中一个当事人至今还在,另一个是否在世我不太清楚,按年龄推算,应该已经去世了。不仅在藏地,包括在汉地等其它地方,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公案。这种为了维护其它众生的生命,而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精神和行为,就是最上等的戒杀。
事到如今,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低贱”的动物而舍弃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又会如何选择呢?也许很多平时将佛理讲得头头是道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却只能闪烁其辞,环顾左右而言他了。
很多人都自诩为了不起的大乘佛教徒,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内心深处的软弱就会暴露无遗。请大家衡量一下,自己是否有堪称大乘佛子的资格?如果没有,就应坦然承认,而不要自命不凡。如果现在能有为了众生而舍弃自己生命的决心与勇气,不论将来是否能够做到,也算得上是守持上等戒杀之人。
对于每个人而言,从无始以来心相续中所积累的杀生罪业是非常严重的。而杀生的果报,就是惨堕地狱,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这一世养成了浓厚的杀生习气,下一世也会因串习而酷爱杀生,并在以后的生生世世都酷爱杀生,也因此而积累更多的杀业,如果不设法让它中断,就只能在地狱中永世不得超升了。
(三)佛经中的戒杀定义
佛陀在佛经中说道:如果在房间内发现有蚂蚁、蚊子、蟑螂、青蛙、螃蟹之类的小生命,纵使它们没有太大的罪过,其存在也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或者因为老鼠会吃掉衣服、食物等东西;或者在睡眠的时候,一些小生命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将自己从美梦中吵醒,在这种日常生活被打扰的情况下,即使感觉不方便,也尽力忍受而不杀害这些众生,就是一种戒杀;
但一般人的行为却并非如此。一旦某种生命的存在对自己稍有不利的影响,就会千方百计地去消灭它,只是碍于法律、舆论的制约,才不敢去杀害同类,否则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佛陀又说道:如果在青稞、大麦、小麦等粮食中发现有小虫,便考虑到:“如果将这些粮食送到磨坊去推成面粉,就会碾死这些小虫;而将这些明知不能食用的粮食销售出去,不但不能转嫁罪过,反而会有偷盗的过失。”为了避免这些情况,于是自己不食用,也不卖给别人,则也是一种戒杀;
当牛、马、骆驼等牲口因为驮运货物过久、过重,而引起背部溃烂生疮,疮口里面繁殖了很多小虫的时候,就不再让这些牲口去驮东西,而且还用柔软的鸟翅羽毛,将这些微小柔弱的生命从疮口中取出,并放到安全的地方;或者在发现肉食中孳生小虫的时候,就不食用、不销售,也不用来喂养猪狗等家畜,并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小生命安全;如果发现被褥下面存在啃食、损坏垫褥等东西的小生命,也不去伤害;或者在走路的时候,虽然知道无意间踩死蚂蚁等小生灵不是罪业,但也小心翼翼,尽可能地不伤害它们。以上这些善待生命的态度,都是戒杀;
上等的戒杀,就是在内脏器官中寄生了虫类,如果不杀死它们,自己不但会疼痛,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打死它们,就可以结束痛苦,获得健康。在面对这种重大抉择时,也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而不伤害其它生命的行为。
佛陀又说道:什么是戒杀呢?如果在仅剩的食物中发现了虫子,若将这些虫子放到其它地方,它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不吃这些食物,自己又会饿死。于此紧要关头,宁可自己饿死,也绝不伤害众生,就是戒杀。
以上内容,就是佛陀在经书中所宣讲的戒杀概念。这些要求不是佛陀对大乘菩萨特有的要求,而是对大小乘佛弟子的共同要求。
我们以前总以为,自己不去饭店中点杀鸡鸭鱼兔,也不亲自去宰杀猪马牛羊等,就算是戒杀。这虽然是戒杀的一部分,但戒杀还有很多细微的要求。在了知这些要求之后,我们也应该尽力去做到。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三种不同层次的戒杀,以及佛陀所宣说的戒杀概念。
(四)综述
有人会认为佛教的这种要求太过分、太不近人情,简直是匪夷所思,但不论是否理解,佛就是这样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地珍爱生命。现在满世界都在提倡珍爱生命,但他们所珍爱的对象,只是人类自己的生命。而佛陀所指的生命,却不仅是指人类的生命,而是包括蛔虫在内的所有生命。只有佛陀,才是珍爱生命的典范,将博爱的意义发挥到了极致 ; 也只有在佛陀的博爱世界里,才没有任何片面、偏袒、狭窄、自私的成分。由此可见,佛不但在宣说如来藏、空性等胜义谛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劝诫后人善待生命方面,也是如此。
既然我们自称为学佛的人,就应当按照释迦牟尼佛的要求去做。比如说,遭遇疾病的时候,不但自己不去服用杀灭寄生虫的药物,而且也力劝他人放弃这一念头。是否堪称佛教徒的试金石,就在于生死关头能否严格履行佛陀言教。如果仅仅在平时精进地磕头、念经,外表看起来非常虔诚,但遇到具体情况的时候,却仍然怙恶不悛,随意违背佛陀教言,就不配进入佛教徒的行列。
如果根本没有善待动物的心,只是一味地去接受各种灌顶,拜见很多上师、活佛,修持所谓的“大圆满”等等,都是没有用的。连佛陀的最低要求都做不到,又怎能修高层次的法呢?
我目前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从这些方面入手。高层次的要求做不到,是可以原谅自己,理解自己的。比如说,如果不能证悟大圆满,生起次第的本尊观想得不清楚,或圆满次第的气脉明点修得差劲,我也不会伤心失望,不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大圆满、生圆次第等等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可以证悟的,我离证悟这些高深之法的境界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没有必要勉为其难。但如果我发现自己连佛陀的最低要求都达不到,居然在小的基础方面停滞不前,就会伤心失望甚至万念俱灰。
不知道你们是怎样要求自己的?是往高处着手,还是从低处落脚?如果选择的是前者,我就不得不告诉你们,这种眼高手低的选择是错误的,我们只能从最低处起步,先奠定好坚实的基础,才能一步步地往高处走。
在座的人当中,很多人的岁数已经不小了。在几十年人生历程中,你们也耳闻目睹了很多令人动容的事情,但是否看到世间有哪一本书有这种善待生命的要求?或者听到世间有什么人是严格遵循这种要求去做的呢?虽然西方也有一些动物保护协会,我们也非常赞叹、随喜、敬佩他们的行为,但在有人申请做动物试验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批准。而佛却不会开许这种做法,绝不允许任何人为了任何目的,去剥夺其它生命生存的权利。
按理来说,任何生命都有生存权和自由权,虽然杀戮行为也不时地在自然界中发生 , 但除了人类以外,没有哪个生命会自认握有对他众的生杀大权。人类的蛮横无知常使其变得禽兽不如,往往仅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凶残地侵犯其它生命,直至物种灭绝的地步仍不为所动。
希望大家不要再对这一切充耳不闻,也不要仅仅将这些要求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付出实际的行动。今天讲完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客观评价自己的基础上,尽己所能地在以上三种层次中,作出符合自己的选择,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严格遵照执行,尽量以自己的行动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五)戒杀的功德
1.现世的功德
佛经中说过:诸佛菩萨、世间神灵都会对戒杀行为感到满意、高兴,并竭力赞扬戒杀之人。
也许有人会想:诸佛菩萨是否会了知我的戒杀之愿呢?关于这一点,相信很多对佛教常识有稍许了解的人,都会轻而易举地作出解答。我们也有无数的例证可以证明,佛陀是全知的正量夫。
另外,戒杀之人还可以获得健康。当然,如果前世的杀业重于今世的戒杀功德,或因为其他原因,就仍有可能会生病。但发誓戒杀之人即使偶感小恙,却可以代替堕入地狱的巨大痛苦。
戒杀之人纵使到了晚年也是耳聪目明、五根敏锐。
戒杀还可以消除寿障,延年益寿。有很多人在遭遇寿障之际,会惊恐不安地延请僧众念诵很多仪轨。其实,念诵仪轨虽有作用,但最奏效的方法,无疑是戒杀。通过戒杀,就可以遣除所有的寿障。
戒杀之人不仅可以得到佛菩萨的庇护,就连世间的罗刹、魔鬼等非人,也会保护此人。护法以及其它世间神灵,也会昼夜围绕,严加守护。
很多居士都在坚持供护法,并念诵格萨尔王等各种护法仪轨,但如果不吃素戒杀,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能戒杀吃素,则仪轨可念可不念。即使不念,护法等鬼神也会履行保护、照看戒杀之人的责任。
以上这些戒杀的现世功德,都是佛陀亲口所说的。
2.后世的功德
经书中讲了很多戒杀的后世功德,归纳而言就是:在没有出离心、菩提心以及特别回向的情况下,戒杀之人来世可以投生为天人。
戒杀、放生还有一个重要功德,就是可以成就戒杀之人的任何一个心愿。
比如说,如果在戒杀放生时发愿:愿我能以此功德,而成就阿罗汉的果位,将来就会成为阿罗汉;如果发愿:愿我能以此功德,而成就缘觉的果位,将来就会成为缘觉;如果发愿:愿我能以此功德,而成就佛的果位,将来便会成就佛的果位。其它愿望也可依此类推。愿力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在有了戒杀放生功德的配合之后,更会如虎添翼,成就所愿。
因此,在我们每次放生结束,念诵《普贤行愿品》作回向时,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特殊机会,尽力地强调自己的心愿。要知道,这时的回向之力与平时是迥然不同的。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谁?
道家创始人老子——
老子生平简介
生卒年不详。据《史记》中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后,对弟子说过老子"其犹龙邪"这话,意为老子像龙那样雄伟,境界深不可测。其实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老子其人到底是谁,早在太史公时代已成了疑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周守藏室之史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也就是说,当时有三位可能是道家的老子,一是李耳(早于孔子),再是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三是太史儋(后于孔子)。太史公大致认为道家的老子便是李耳,但近代学者只有胡适、张煦、马叙伦几位继承了该说法。一般都认为是老子其人其书应当在在孔子之后,如梁启超、冯友兰、顾颉刚等学者。还有人折中前两者意见,如唐兰主张老聃与孔子同时。钱穆则明确指出老子应在战国晚期人。
老子出世传说
春秋时期,鹿邑县,名叫苦县。城东十里,有个村庄,叫曲仁里,这里松青柏翠,水秀山明,算得上一个风景佳丽的宝地。
单说村前有条赖乡沟,沟水清澈见底,两岸李树茂盛。在那李子树林深处有一户人家,这家闺女,年长一十八岁,模样俊俏,花枝招展,知书达礼,典雅温柔。爹娘把她看成掌上明。这闺女有个别脾气,发誓终身不嫁,一生守在二老身旁,安心攻读诗书,侍奉爹娘。
一天,这闺女到乡沟水边洗衣,在石头上搓了一阵,举起棒槌“梆!梆!梆!”刚几下,就见两个对肚儿长在一起的李子从对面不远的水面上漂了过来。她停下手中的活计,伸手把李子起来。只见两个李子都是一面鼓肚儿,一面偏平,象两个耳朵合在一起。这李子红里透黄,黄里透红,放鼻尖上一闻,喷香喷香!咬一口尝尝,蜜甜蜜甜!里面还有品不尽的后味儿。她几口就吃完了。
刚吃完李子,她就感觉心里难受起来,腹痛难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下腰,捂着肚子,脸得象铜片一样。就在这时,肚里有人说起话来:“母亲大人,莫要难过,等孩儿坐正也就好了。”她大吃一惊:怎么李子变成胎儿啦!她红着脸,小声问肚里的小生命:“孩儿,你然已经会说话,就出来吧。”胎儿回答:母亲,孩儿眼下不能出去。我要在这里想事哩!”“想啥事?”“想啥?能使傻子聪明,笨人变灵,恶者向善,天下太平。”“那你啥时候出来?”“等到天长严。。。。。。牵骆驼的来。”往下不说了。
花落了,花开了,花又落了,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孩子还是没有降生,吃李子怀孕的闺女害怕了,她偷偷跑到一个背静的地方,小声问肚里的娇儿说:“儿啦,人怀孕了,都是十个月生,你都一年多了,咋还不出生呢?”胎儿问母亲:“天长严没有?牵骆驼的来了没有?”母亲说:“都没有。”胎儿说:“时候不到,我不能出世,出世就害了你。”
树叶青了,树叶了,又一个年头过去了。吃李子怀孕的闺女偷偷跑到村后大李子树下,求胎儿说:“儿啦,我怀你都两年多啦,应该生了?”胎儿说:“天长严没有?牵骆驼的来了没有?”母亲说:“天没长严,牵骆驼的没有来。你老是问这干啥?”胎儿说:“时候不到,我还不能出世”。
八十一年过去了,吃李子怀孕的姑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她走进了自己的屋子,坐在床前,问肚里儿子说:“儿啦,我的冤家,整整八十一年啦,你还不应该出生吗?”儿子又问那句老话。当母亲的心里想:“天还有东北角一块没长严,牵骆驼的至今没有来。他老问这两句,还说不能坑害我,到底是怎么啦?唉,管他坑害不坑害呢!我就说天长严了,牵骆驼的来了。”想到这,就对肚里儿子说:“天早长严了,牵骆驼的也来了,你快出生吧。”话音刚落,儿子就顶断母亲的右肋,从里边拱出来了!咦!原来是八上白胡子小老头!连头发和眉都白了!
母亲和右肋流血不。儿子见牵骆驼的没有来,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慌了手脚,我也没法撕下骆驼补在您老肋上的,这该怎么办呢?”说着,双膝跪下,给亲磕了三个响头。母亲说;“儿啦,别哭了,我不埋怨你。你是为娘吃李子怀孕生下的,那李子又象两个耳朵合成的,娘给你指姓起名,唤李耳吧!临死之前我没别的话讲,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娘进入之后,你在尘世之上,做个好人,也就不枉我怀你八十一载了。”说罢,绝气身亡。李耳跪在母亲尸首旁边,好在痛哭一场。
因为李耳出生是老头模样,后来人们就把李耳称为老子。
孔子问礼
鲁国的孔丘苦苦钻研礼的学问,可终没有得出结果,为此,他感到十分苦恼。当他听说老子经过多年苦心探索钻研,知识渊博,已经求得天道的消息后,就决定拜访老子。他带了南宫敬叔一起来到周的都城洛阳。
老子看见孔子,便热情地问道:“你来了,我听说,你现在已经成了北方的贤者,可不知你是否已经懂得了天道?”
孔子回答说:“我还没有懂得天道。”
老子又问:“那么,你是如何去探求天道的呢?”
孔子回答说:“钻研‘礼、仁义’,以制度名数来寻求的。到如今已有整整五年的时间了,可是还没有得到。”
老子又问:“你又怎样继续去寻求呢?”
孔子回答说:“我是从阴阳的变化中来寻求,已有12年了,可仍然没有得到。”
老子说:“是啊。阴阳之道是眼睛不可看到,耳朵不可听到,言语不可表达,是通常的智慧所不能把握的。因此,所谓得道,只能是体道,如果试图象认识有形、有声之物一样去认识道,用耳朵听,那是听不到的,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到的,用言语去表达,也是没有合适的言辞能够表述清楚的。”
老子稍微停了一下,看了看孔子,又继续说:“你说你寻求了十二年而不得,那是当然的。如果道是可以奉献的,那么,人们就没有不把它奉献给君王的;如果道是可以进贡的,那么,子女就没有不把它进贡给父母的;如果道可以告诉别人,人们就没有不告诉兄弟的;如果道可以给予他人,那么,人们就没有不给予子孙的。然而,这些只是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就是道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言、不可赠送。寻求道,关键在于内心的感悟。心中没有感悟就不能保留住道;心中自悟到道,还需和外界的环境相印证。因此,可以说,得道之人是无为的,是简朴而满足的,是不以施舍者自居,也无所耗费的。自己正的人才能正人,如果自己内心不能正确领悟大道,心灵活动便不通畅。”
临别时老子对孔子说;“富贵的人用钱财送人,有学问的人用言辞送人,我不算有学问的人,但还是送给你几句话吧。老子停了一会又说:“孔丘啊,你要恢复的周礼已失去生命力了。你时来运转时就驾着车去做官,生不逢时就象蓬草一般地随风旋转。要知道善于经商的人总是将货物藏起来,好象什么也没有;有高尚道德的人容貌谦虚的像个笨人。抛弃你的骄气和过高的欲望吧!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老子的一席话,对孔子触动很大,他对自己的学生说:“鸟,我知道它们善飞;鱼,我知道它们善游;兽,我知道它们善于奔走。对于鸟,可以用箭射它;对于鱼,可以用网捕捉;对于兽,可以用陷阱擒获。至于天上的龙,我不知道龙的形状,也不知道它是怎样乘着风飞上天的。我今天看见了老子,就象见到了龙一样啊!”
箴言名句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关于老子之道的几个问题
老子之道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阐述,因而,如果存在不同乃至相反看法,都是自然、正常的现象。不同看法之间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加深对老子之道的理解和认识。
一、老子之道是否实际的存在?
老子之道究竟是实际的存在,或者只是概念上的存在?这个问题是由陈鼓应先生提出来的。他自己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道’只是概念上存在而已。‘道’所具有的一切特性的描写,都是老子所预设的。”(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这个回答恐怕并不符合老子作为一位中国古代先哲的思维特性。
按这种说法,老子关于“道”的一切特性的描写,就仿佛一位数学家在随意构造、推导关于纯数学方面的定理,而不受任何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若是如此,这个“道”不仅“可道”,而且是“恒道”;这个“名”不仅“可名”,而且是“恒名”。但是,老子不仅明确地指出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老子•1章》),而且说明观察、体悟“道”的方法,就在于“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1章》)。这表明老子之“道”并非纯数学的智力游戏,而是反映了一种客观实在。事实上,尽管老子道论具有丰富内涵,但不管是哪一种意义的“道”,无不是从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中思考、体悟出来的。特别是,从修道、体道角度而言,这种“道”就更加离不开每个人的亲身实践和经验。牟钟鉴先生说得好,《老子》“段段饱蘸体验”(牟钟鉴等主编《道教通论》,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49页)。老子关于“道”之特性的描述,诸如自然、无为、虚无、清静、纯粹、素朴、平易、恬淡、柔弱、不争等等,无一不是“饱蘸体验”的。其中,“自然、无为”最具根本性意义。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道恒无为而无不为。”(《老子•37章》)这两条特性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可以归结为“自然无为”。这既是“道”本身的特性,因而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同时又具有修道的方法论意义。所以,老子之道不是一种所谓“预设”的模式。
二、老子之道是西方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吗?
与上述“预设性”颇为类似的一个看法,是张世英先生提出的所谓“旧本体”说。他认为,老子所讲的关于本体论的“道”,是“常道”,是超验的普遍永恒的东西,因而基本上是一个“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这个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从天人关系角度看,作为本体化范畴的“天”(即“道”),一方面具有绝对性、无限性,同时又是发育万物,大化流行的过程;而人的本体取决于“天”,人禀受“天”所赋予之性,所以也具有绝对、无限的超越本性。故此,从本体上而言,“人”与“天”是合一的。尽管这种合一还只是潜在性、自在性的。另一方面,从人作为现实中的个体存在而言,又是有限的、相对的,与“天”是有所区别的。这种区别不仅是自然的客观存在,而且也反映到人的思维意识之中,这样就出现了“人自人,天自天”的相分情况。
但是,这种天人相分情况至多只能是暂时“遮蔽”那种潜在的、本体意义的天人合一,而不能从根本上取消它的合一性。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按照中国传统哲学,人的存在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是形神合一、身心合一的整体存在,并没有西方那种灵魂与肉体相分离、精神与物质相对立的二元论。”(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所以,老庄道家哲学有助于探索、解决那种灵肉分离、天人相分的“异化”现象,使人“复归”于天,从有限中把握无限,在相对中达到绝对,从而达到安身立命、天人合一的目的,所谓“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真人”所达到的这种天人合一境界,是有其哲学根据的。首先,从本体论角度而言,“体道”的哲学根据是“道通为一”(《 庄子•齐物论》)和“万物皆一”(《 庄子•德充符》),即所谓“通天下一气”(《 庄子•知北游》);其次,从自然本性和存在方式角度讲,“自然无为”是“道”的存在特性,从而也应该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及其存在方式。所以,“自然无为”作为一条基本的体道方法,其实正反映了人类“复归其根”的自然本性。总之,老子之道所具有的注重修道、体道,与“道”合一的特色,决定了老子之“道”不可能是西方哲学史那种“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
三、老子之道的“有”“无”论是否矛盾?
有些论者认为,在宇宙生成论方面,老子认为具体存在的“有”总要有一个开头,而这个开头的东西就不能再是“有”而只能是“无”。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上万物都是以“有”为生的,有的都是具体的物质形态的转变,决没有从绝对的“无”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老子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有时又把道说成是包含了物、象和精的一种混沌未分的最初物质,这样一来,道也就不再是“无”而是“有”了,从而又与“无”中生“有”的说法发生了根本的矛盾。总之,老子一说道有物,一说道无物,从而使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关于老子道论的矛盾问题,其实并不是老子道论本身存在矛盾,而是后人的理解和认识产生了矛盾。理解和认识老子道论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在方法上要注意老子论道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二是老子所谓“有”与“无”,均属宇宙本体论与生成论范畴,“有”与“无”不过是针对“道体”的存在及其演变、发展历程中的不同性状、状态而已。从存在论(即本体论)角度而言,老子讲的“无”并不是要否定掉宇宙万物的本体;从生成论角度来说,“无”也不是要否定掉宇宙万物尚未形成、阴阳二气尚未分化的混沌整体这一根源。董光壁先生指出,老子的“无”相当于现代物理学中的“基态量子场”。 现代物理学也改变了人们对“真空”概念的认识,它并不是指任何东西都不存在的虚空状态。“按照量子场论,各种粒子都是真空的激发态,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由真空激发形成的。‘真空’回到了老子的包藏着无限生机的‘无’。”(董光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这个看法甚有科学研究的参考意义。庞朴先生从文字学角度指出,古人关于“无”的认识存在三个阶段:一是“亡”,指有而后无;二是“无”,指似无实有;三是“无”,指无而纯无。老子所谓“有生于无”的“无”,原为“无”字。(庞朴《说“无”》,见《一分为三》第271-282页)这也说明老子关于“有生于无”的说法并不存在矛盾。所以,不宜把老子哲学中的“无”理解为什么东西都没有、绝对虚空的“无”。 三是要把握老子关于“道”的描述的语言艺术,这一点牟钟鉴先生说得很透彻,所谓“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领,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 牟钟鉴等主编《道教通论》第70-71页)。所以,应该把老子所谓“无”理解为一种正言若反的语言表达艺术。
四、老子之道不讲道德吗?
张世英先生认为,“《老子》的‘天地不仁’更明确地取消了道和天的道德意义”,“《老子》的‘道’是人道的对立物”(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第364页)。很难想象,老子的《道德经》居然会取消道德意义、居然是人道的对立物!
在老子看来, “道”固然是万物的本根、根源,但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形成过程,还离不开“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51章》),可见,“德”对于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形成过程来说,亦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而“德”之所以具有这种重要作用与意义,是因为“德”与“道”有着密切关系,所谓“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老子•25章》)。意谓“道”为主,“德”为从,“道”决定了“德”的特性,“德”体现了“道”的性质。《管子•心术上》也讲:“德者道之舍,……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意思是说,“德”就是“道”的体现,万物依赖它而得以生长,心智依赖它而得以认识“道”的精髓,所以“德”就是“得”。所谓“得”,即是说所要得到的东西(“道”)已经实现了。无为叫做“道”,体现它就叫做“德”,所以“道”与“德”没有什么分别。正是由于“德”与“道”有着密切关系,决定了“德”对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形成过程的重要作用与意义。特别是,对“人”而言,在老子之“德”主要指人的纯粹本性(所谓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55章》))和修养境界(所谓“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老子•65章》))。
所以,老子之“道”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哲学范畴,而且更是一个关于人的内在本体和价值的形上学范畴。“道”的本性是“自然”的,所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老子•51章》)。这所谓“自然”,是指“道”的存在状态、方式与过程,并不是排斥人类之外的自然界,而是关系到人类生命的实践准则及其意义,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老子•25章》)。所以老子之“道”最终是要探究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根源,解决人的价值本体的形而上之根据,即所谓“安身立命”的问题。所以,对人而言,老子之“道”只是作为潜在的基础,要靠人的自觉实践、体验(即所谓“践道”、“体道”),才能把潜在变为现实,与“道”合一,获得自由。这就是老子之“道”作为本体论范畴所蕴涵的“人道”意义,从中显示出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五、“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否可信?
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有一段常为后人所称道的话,即:“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回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尊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纵览古今,这段话很有代表性,道出了古往今来芸芸众生内心里共同的困惑。那么,应当如何深刻理解“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以及伯夷、颜回这类现象呢?
在老子看来,“天道”是自然无为的,故而“无亲”;之所以“常与善人”,是因为善人合于(或同于)道、合于德,而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老子•23章》),由此便可谓天道“常与善人”。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所谓“常与善人”,是指充实或丰富他这个人(善人)内在的道德品性,也即充实、光大他内在的人性之美,而非“与”(给予)他以别的什么东西。而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善人”自为的结果,而非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在暗中帮助他。我们还可借用《庄子•列御寇》中的一句话来解释:“夫造物者之报人也,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所谓“造物者”,就是指“天道”;所谓“其人”,泛指某个人,引申为人在社会中的名利地位,祸福荣辱等;所谓“其人之天”,指人内在的自然天性、本性、德性等。综合起来,大意是说,上天(天道)对人的回报,不是回报他人间的祸福荣辱,而是回报他本人最内在、最本真的天性本性。总之,“善人”如果真善,那么“善”本身就是上天对他最好的、最真实的回报了。行仁得仁,何复他求?反之,“恶人”若真的作恶多端,那么,“恶”本身即是对他个人最内在、最本真的天性、品性的戕害和毁灭。他的心灵是污浊的,他的境界是卑劣的,毫无“天爵”可言。这就是上天对他最严厉的报应了。至于“人爵”再高,权极一时,或荣华富贵,显赫一生,亦何足道哉!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如此,可谓善人矣!颜回好学,三月不违仁,可谓真能践道而成就其德性矣!这就是天道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盗跖之徒,纨绔子弟,其或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但终有命归黄泉的一天。不亦悲乎!何以为寿?何足为贵?
总而言之,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存乎其人,存乎德行!
庄子——
庄子生平简介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战国蒙(一说是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另一说是今安徽蒙城县)人,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哲学家。他以其代表作《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经》)阐发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展了道家学说,使之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
庄子事迹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吏、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他做过蒙城漆园(在今县城涡河北岸的漆园故址)吏的小官,但不久辞去。他布衣草鞋,糁汤野菜,安居陋巷著书。生活难以维持时,曾向监河侯借过粮食。楚威王闻境内庄周是有学识而贤德的人,就遣使备千金厚礼前来漆园(蒙城),请庄子为楚国宰相。使者言明楚王许以为相的旨意后,庄子笑谓楚使说:“千金可算是重礼了,相位可谓尊贵至上。可是,你没见祭祀时的牛吗?人们把牛喂养肥了,祭祀时披红挂彩,还不是牵到太庙杀了作祭品?我宁愿在淡泊无为中度日,不去做牺牛”庄子在谈笑中“喻牛辞相”,终未为楚国宰相。
战国初年,诸侯兵戎相见,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在这 样的社会背景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学术流派竞相而起,形成了他独特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畔,相距仅百里,故又称他们的学术思想为“老庄涡河之学”。
庄子晚年常垂钓于濮水(今城南芡河)、涡水,游于濠梁(今安徽凤阳临淮城西南)观鱼,与鱼鸟共乐,甘于清静闲居的生活。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皇帝颁布沼书,赐号庄子为“南华真人”,称其书曰《南华真经》。
后世评论(来自网友)
(1)诗的婉约、哲的彻悟尽现于庄子
庄子的思想在当时勿庸置疑带着些许反动色彩(此乃笔者浅见,如有不同意见,欢迎批评指正),例如“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太尖锐、太深刻、太恣意,亦因此不被各路诸侯所采纳,尚幸他一不求位高权重,二不求锦衣玉食,于是乎依旧做他的漆园吏,依旧著他的《逍遥游》,依旧藏身于陋巷之中,咀嚼着那口饿不着撑不死的俸禄。庄周不若孟柯斗志昂扬地游说诸侯逞尽辩才,“他只在僻处自说”(朱熹答问是云)一径任满腹经纶跃然纸上,任才华横溢细水长流。
历史之流宛如滔滔江水,颇有一泻千里、永不回头之势。奴隶制的西周绝迹于诸侯割据的滚滚烟尘,继之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尔虞我诈、混战厮杀——大一统前的四分五裂是这方广阔而灵秀的土地在重生前最后的阵痛!
庄周并不是在这场撕心裂肺的阵痛中唯一挣扎的人,他能够在最终潇洒地淡出而不是狼狈地逃遁是我最初对他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他曾用一只环来比喻社会,说人世间的一切冲突搏杀、你死我活、血溅泪洒皆在环上进行;环上的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斗争双方的立场;如你不想有危险,就只能悬浮在圆环的空虚处,环上的是非,你不必参与——对事物的演化,既不应去推动,也不应去抵制,最好是顺其自然。当时觉得这样的观点太消极、太圆滑,不像大丈夫所言。看过“文景之治”,才发现:对于没有太过丰厚物质积累的社会而言,无为而治似乎存在得更为合理。
有时觉得庄周难免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他一生渺看世事若过眼云烟,又时而对世情冷暖出言批驳,词锋锐利毫不姑息。庄周一次见梁惠王时身着麻布长袍,襟上补疤,提脚跨上阶陛时,袍带和鞋带都挣断了,惠王问:“庄先生为何如此窝囊?”庄周说:“不是窝囊,贫穷罢了。读书人有抱负没法施展,那才是真窝囊。读书人窝囊,皆因生不逢时,正如鄙人。你看那跳跃在树梢上的长臂猿,让它栖息楠梓樟一类的乔木林,攀缘高枝,往来自如。若斩尽乔木逼它逃入钩棘臭橘一类有刺的灌木丛,行动躲躲闪闪,一身战栗,难道是抽筋断骨了吗?当然不是。处境不妙,无法施展自己的本领而已。现如今,上坐昏君王,下立乱宰相(惠施),有抱负的读书人夹在中间,要不窝囊,谈何容易!”
如此这般的措辞,梁惠王自然不敢恭维,这大概也就是才高八斗的庄周为什么捞不到一官半职的原因了。
我又觉得庄周难免是有些无辜的。年轻时的才华外溢、不知韬晦竟曾引得知交惠施彻查梁国都城三昼夜搜捕之,只因担忧庄周要抢他相爷的肥差。惠施永远都不会相信——庄周只是基于一份真挚的友情、一腔念旧的热情,才远道赶来的——很久不见,想看看朋友——仅此而已。
诸子百家,缘何独独钟情于他呢?
也许是因为……他为人够傲,损人够酸,文章够辛辣,文采够光芒。的确,他活得不够四平八稳,活得不够风光煊赫,但是,我要说,他活得够恬淡、够畅然、够舒逸、够内涵、够浪漫。灼人的烈焰是他的内核,绝对的洒脱是他的内在,嶙峋的怪石是他的风骨,碧空的游云是他的情怀!
论忠君爱国,他不如屈原——前者尽己之能辅佐怀王,受诽谤遭流放仍与楚国誓同生死——而庄周则譬如一羽散居在山林的野鹤;论劳苦功高,他不如孔子——前者历尽坎坷周游列国,虽真知灼见不为所用仍兢兢业业教书育人——而庄周则恰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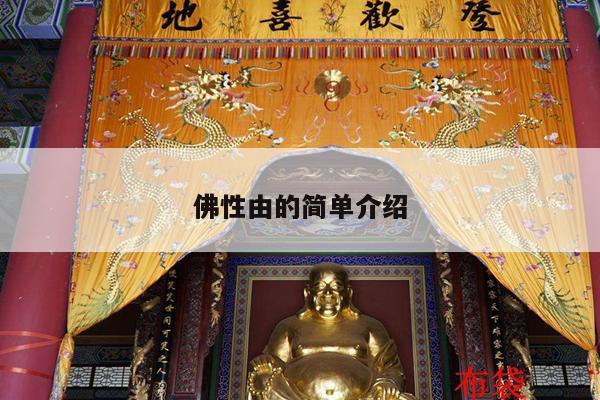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谁帮忙详细解释一下
第一章: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Jiao)。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可道非相辅相成的根源,才是永恒的道;名可名非相互所指的本来,才是永恒的名。无名,是万物的元始之时;有名,才有了万物的根本所指。因此,常归溯到无形无象无欲念处、便可观想到无名无穷的微妙;常从有形有象有欲念处、便能观察有名有限的边际。这两者其实是相同、只是定名不同而已;同样可说是玄,玄之又玄,是一切奥妙的门径。
这一章是《道德经》全篇经文的总纲,要仔细体会。
老子在首章便以精简、独到的文字“提纲挈领”直接揭示了“道”是“宇宙生命”的总根源。亦即“道”就是宇宙生命的最终极根本,通俗地说,一切一切都来源于“道”。
如今我们可以借助科技的“眼睛”认识得更清:这个宇宙生命整体中,悬浮着无数个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星球”。各个星球之间看似“随意”悬浮着,彼此之间却又有着某种“规则”互相牵连。
这些星球是由什么能量产生的?又是什么力量使它们彼此独立又相互牵连?
老子在2500年前就深入思考了这些生命问题。只不过老子的“思考”和“观察”不仅仅用“目”,而是凭借其“心”。甚至可以认为老子是将一切粉碎,回到根源的“无”,追溯到一切最根本的本来。
老子惊世骇俗提出:“道可道非,常道”。
《道德经》全篇经文的根本核心就是这“道可道非、常道”六个字。理解这六字,老子全八十一篇经文的本意便迎刃而解。
“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可道非”便是宇宙生命体系中的一阴一阳两股力量,两股作用,或者说两种能量,抑或说两种存在。有阳就有阴,有阴就有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它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就是“道”,也就是宇宙生命整体。
道可道非相辅相成的根源,乃是永恒的道。
在这里,必须先明确“道”这个定义。
“道”这个“名”并非是绝对就有的。老子在第二十五章中明确指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因此,“道”只是老子给“宇宙生命这个整体”的来龙去脉勉强取的一个“名”。
另外,还必须理解,“道可道非”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若说是一个东西,可它偏偏是“道可”和“道非”的“二”;若说是两个东西,它却互相融合成“道”难以分割,又明明是“一”。
我们不妨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
任何一件事物,有“赞成者”,有“反对者(不赞成者)”,还有“中立者(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里“三”种意见其实只有两种组成,就是“赞成”和“不赞成”,但都只是在说同“一”件事情。并且,这里的“赞成”和“不赞成”并非也是绝对的“对立”。“赞成”有可能是“90%赞成+10%不赞成”,如此说来,仅仅是“赞成”就有无穷个可能。但只因“规则只有三项”,并且只能确定一种选择,只好定为“赞成”;“反对”和“中立”也一样,不是绝对的“反对”,也没有绝对的“中立”。
这里面就涵盖一个“相辅相成”作用的意思。
“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非相辅相成的根源,才是永恒的道。
这句话中包含有三种含义在内。
一是,“道可”或“道非”都不能“单独存在”,或者说都不能“单独发生作用”。类似于“独阳不生,孤阴不长”。
二是,“道可道非”并非是说一个“道可”和一个“道非”。而是意思说“道可”中有“道非”,“道非”中也有“道可”,因此说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亦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三是,“道可道非”相互作用的“能量”或者说“根源”,是因为“道”才永恒不灭。反过来说,没有“道可道非”的相互作用,就没有“道”的“永恒存在”。
至此,我们就要理解到,宇宙生命整体就是“道”。
“道”外再无任何“物”。这便是庄子说的“至大无外”。
而这个“宇宙生命整体”之“道”的生命运行就只是“道可道非”无休止的相辅相成,循环往复。
这个“道可道非”的作用是“本来就如此的”,是“无色、无声、无象”的。比如一朵花,它是如何开放的,“内部”有何能量促使这样变化,这一切都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触摸)之不得”的。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因此,“道”也是“至小无内”的。
但是,这朵花之所以开成红色,那朵花之所以开成蓝色,这全是“道”的主宰。“道”可令花为红,“道”也可令花为蓝。可令花谢,可令花开。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除此外,“道”外无任何“物”有能力能改变这个“根本”。
有人说,“人”可以把红花变成蓝花,通过染色或移植。殊不知,这些技术的发现,也是“道”令人类才有的发现。即便是发现了,移植技术的“内部变化”依然是“道可道非”在作用。从根本意义上说,“人”和“花”其实都是“物”,具体说明在注解“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这句时会阐述。
因此,我们可领悟到,宇宙生命整体中只有一个“道”在运行,这个运行就是“道可道非”,无论是地球围绕太阳,还是地球上的和风细雨……除此外,无“其它”事。
简单理解就是,宇宙生命整体中,只有“道证明道”这一件事情。一切星球运行,一切人类活动都只是一种“相对假象”。
这个理解需要谨记,在整个之后的八十章经文都是这个定义的应用。
因此,我们要理解老子的经文思想,必须建立一个“整体”的概念,亦即说、看待任何事情,任何一物,任何一个念头……都要明白“它是一个整体”,而对待这个“整体”时,我们“常人”只能是知晓“其中一部分”而已。即便是人类在“道”中,就犹如沙滩上的“一粒沙”。
老子通篇经文中,常用到“圣人”这个指称。老子经文中的“圣人”是指“心合了道”者。“圣人”区别于“常人”的根本就在于,圣人始终立于“整体”看待一切。那么,“圣人”和“常人”是“二”还是“一”呢?这又回到了上面的分析,他们是“二”也是“一”。就比如说,老子是圣人,很明显,老子已经活在我们的心知中,与我们合为“一”,但只要一提起,又分明老子是老子,我们是我们。
就拿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来举例。
这里的“百姓”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常人”。圣人和百姓已经融于“一心”,但这里的“一心”并不要绝对理解成“一”,而是指“圣人心包含了百姓心”。但是圣人也是百姓,百姓也是圣人。他们之间是“二”也是“一”。
因为任何事物要归顺一个“整体”即“道”,必须时刻展现“道可道非”。当百姓都执着于某种妄念之时,圣人就给予点化。“圣人”的意义就在于平衡任何事物。通俗地说,“圣人”就是“合于道”的“平衡者”。
老子所谓的“圣人”就是“合了道者”。
正因为合了道,因此就是有整全的“心知”,是深明一切来源于“道”,一切顺应“道”,一切又还原于“道”,但“圣人”并不能说就是“道”。
“名可名非,常名”。名可名非相互所指的本来,才是永恒的名。
老子在说完“道可道非,常道”外,紧接着就是“名可名非,常名”,这两句话有什么紧密关联呢?
“道可道非,常道”是说宇宙生命这个整体的来龙去脉的“本来”、“根源”,即一切一切源生于“道”。
“名可名非,常名”是说“认识道”这个本来的生命过程的“名相”显化。怎么理解?
前面说了,这个宇宙生命整体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道”在证明“道”
的周而复始的运行,除此外,没有其它事。意思是,在一开始,连“道”这个“字”也没有,就是“一个混然天成的东西,这个东西自己在证明着自己的运行”
是老子揭示了这个本来,为了表达的需要,勉强取了个字叫“道”。
那么,一朵花开,根本上就是“一个东西在开放着”,是后来人类命名这个开放着的东西叫做“花”。归根结底,人类之所以要给这些“东西”起个名字,也是“道”使然。
而“道”的运行含有“道可道非”无穷的变数,也因此一定会产生“名可名非”的无穷的“名相不同”,这就是“名可名非”。
“常名”是什么?
“常名”就是“本来、本源”。
“花”本来是没有“花”这个“名”的,而“花”本来的名就是“常名”,但“常名”本身无所谓“名”与“非名”。就好比一个婴儿看见一朵“花”,婴儿不知道这是什么、也无所谓这是什么。而所谓的“花”只不过是人类自然活动、相对认识的一个“记号”而已。
当今,我们是相对比较容易举例领悟老子的本意的。
同样是“花”,在英语地区名叫“FLOWER”,在日语地区名叫“HANA”,在汉语地区名叫“HUA”,这便是“名可名非”。有人这样名叫,就一定有人那样名叫,这是由“道可道非,常道”决定的。但是“常名”无法命名,“常名”是由“名可名非”所指的那个“本来”。通俗地说,“常名”就是那个“命了的名+尚未命的名”的那个“名”。
东方的老子将“宇宙生命总根源”命名“道”,释迦摩尼命名“佛”,同一个“根本”却出现两种名释,这也是“道可道非”使然。两者阐释的是同一个“本来”所指,名却不同,这便也可看作是“名可名非”。谁可谁非并无意义,抑或两者也有互补。而“常名”正是“道”或“佛”所指的那个本身。
无名,万物之始。
宇宙生命的源头是一个“寂静的混沌的整体”,这个“混沌的整体”就是第二十五章中描述的“有物混成”。“此刻”自然没有名字,即“无名,万物之始”,这里的“万物”是包含宇宙整体内的“全部之物形成之前”。
老子把这个“混沌的整体”勉强取名叫“大”,取个字叫“道”。
被命名字“大道”之后,万物便开始有了各自的“名”,即“有名,万物之母”。
为什么要称为“母”呢。
这是老子大智慧的恰当比喻,是想让众人容易明白。
天下的女性,追溯到最终都是“道”所化生。“女性生孩子”,这是“道”的能量使然。女性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女性就是孩子的“母亲”,孩子便是母亲的“子”。这“母”与“子”便是“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有了名,“母”就既知其“子”,“子”就复守其“母”。
这个例子虽然容易明白,但必须指出的是,“道化生万物”并非等同于“母生子”。“母”生“子”后,由“一”变成“二”,“子”便不在“母”中;“母生子”只是“物生物”,是“有”生“有”。而“道”生万物,是“无”生“有”;万物出现后依然在“道”中,“道”不变,“道”永恒是“一”。
常无欲、以观其妙;“道”无形无象,要体认它的“无生万有”的微妙也必须处在无形无相,并且无欲念的宁静的状态下才可以观想到。
就好比刚出生的婴儿暴露在空气中,婴儿并不知道何为空气,只本能感觉现在和呆在母亲体内时有“微妙的不同”,究竟有何不同,他也无心无言,只是本能的“哭了出来”。
婴儿长成少年,我们让他去描述“当初”的那种“微妙”,他是无论如何也描述不出来的,就因为“本能”已经改变,这也是“道可道非”使然。
长大的少年再观察,就是“常有欲、以观其徼”。
因为这个时候,少年多少似乎有了“心知”。父母告诉他这是“花”,他就会联想,“花是怎么开的?”、“这花那花怎么不同呢?”、“这花什么味道?”奇妙的想象和欲念,也即是会激发太多“名可名非”的思考,而这些所谓太多的诸如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底”就等同于“徼(Jiao)”。“徼”即是“边界、边缘”之意。
没有“名”的“无名”状态和“有了名”的“有名”状态其实指的是同一个“本体”,即“道”;
无名时的“常无欲”之观对象和有了名之后的“常有欲”之观对象指代的也是同一个“本体”,亦即“道”;
这里理解的关键是“常无欲”和“常有欲”的“观”是“谁在观”?
“常无欲”之观,是“道体观道体自己”,或者也可是“合了道”的“圣人”如老子的“观”;亦即俗称的“道观”、“观自在”,自然是微妙无言;这里的“常无欲”重点在“无”,而这个“无”正是合于“道”的恍惚、混沌时的状态。这个“无”其实包含“无限的可能”。
“常有欲”之观,便是“道中的个体观道体”,自然会生出“美之为美、善之为善”的妄断,这个在第二章经文阐述得很清晰。自然也就以“观外在”而观,总想观其究竟。这里的“常有欲”重点在“有”,而这个“有”正是从“无”中化生出来的无穷的形态。但即便是因为“道可道非”相互相成似乎无穷多种变化的状态,但因为此时是“常有欲”之观,是“有心之观”,因此总希望“观”到变化的“边界”,即“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1. 无论万物是“无名”之时,还是“有名”之后,其本来之“物”是“同”一个“物”,只是在从“无名”到“有名”的刹那间,“名”就相“异”了。
在这里要指出,“无名”之时与“有名”之后并不是“等同的有”。
比如说,开始一池静水,是“无名”状态下的静水(权且把一池静水当作解释用的名),之后,池中化生出各种鱼。显然,无名时的池水是“一”个整体,有了各种鱼之后,就有了“多种”“有名”的“物”了。即便这些“物”还在那个“一”当中。
2. “常有欲之观”和“常无欲之观”这两种“观”其实是相同的“观”。当刹那间合于“道体”便进入“无名”的“常无欲之观”;刹那间被“名相”所牵制,便又回到“常有欲之观”,恍恍惚惚、若即若离。
我们不妨再举个婴孩的例子来形象理解。
一个半月大的婴儿爬在镜子前,看见自己,但他并不知道镜子里的“他”就是自己。这个时候,镜子里的“他”就是“常无欲之观”;镜子外的他就是“常有欲之观”。常有欲之观的他便“好奇”,并不断摸索、敲打镜子,试图探究这个“徼”的究竟。
3. 若粉碎时空的限制,“道”中的任何一物,无论是亿万年前的化石,还是现在的树叶,从“道”这个根本意义上说,都是“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因“道”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之后的万物化生之后,彼此的“物”与“物”只是出来之后的“名”不同而已。
此处,归根结底的理解应该是庄子的“万物齐一”。
无论是一头牛和一棵树,还是一个人同一块石头……理解这里,一定不要被“牛、树、人、石头……”这些名相所牵制,而是体悟到“粉碎这一切”,回到混然天成的“无”之状态。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前面1、2分析可知:“无名”和“有名”,“常无欲之观”和“常有欲之观”,彼此“此两者”都可谓是玄妙。加上3所描述的其实更有无数的“此两者”的玄妙不断在幻化,因此就实在是“玄之又玄”。
这正是“道”的活力无穷的显现,是一切奥妙的根本门径。
《道德经》通篇说的是指圣人、太上,也可以说是老子自己的“得道者的体认”,并不是指通常的“个体常人”的想象;不了解这个关键点,读者会陷入迷茫中,会以自己对号入座,试图以自己的理解去想象,因为这种想象会有“名相”的束缚,观点自然偏颇,自然会陷入‘美之为美、善之为善’中。
不过,我们常人仍可以试着进入老子描绘的意境中去体会,也会有一种突破自己的境界的提升,这便是《道德经》作为经典传承带给我们的宝贵之处。事实上,现实中的养生、兵法、权谋、教育、经济、哲学、自然等等所有分科都可以从道德经中汲取、提炼出根本的精髓。
但是《道德经》本身是穷极根本的“经”,是诠释宇宙生命本体的终极;老子的本意是给普罗大众、读者享受他的体认后的成果而已;艰难的证道、修道的过程,老子和那些圣人已经“实践”过了,常人要“修”恐为其难!这或许是老子的“用心良苦”之愿。抑或是老子把“常道”列明开来,由我们“道可道非”罢了。
老子的这一章是《道德经》的总纲。真正理解的核心是“道可道非,常道”。这句没有体悟到根本,之后的经文基本大意就会出现同样的偏离,读者自己可以体会。有的注解说,道德经本来是没有分章节的,是后人为了理解、传述方便就起了八十一章。对此,我们不便妄论,因为没有标准。但是,把拆分的章节“合起来”体悟,就不至于会有太大的偏离。

本文链接:https://www.sjxfo.com/bk/xuefo/956.html
转载声明:本站发布文章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