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缚伽蓝(纳伽是什么意思)

《大唐西域记》卷五六国(3)
五、曲女城附近诸佛迹
城西北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七日说诸妙法。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复有如来发、爪小窣堵波。
说法窣堵波南,临殑伽何,有三伽蓝,同垣异门,佛像严丽,僧徒肃穆,役使净人数千余户。
精室宝函中有佛牙,长余寸半,殊光异色,朝变夕改。远近相趋,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众。监守者繁其喧杂,权立重税,宣告远近:欲见佛牙,输大金钱。然而瞻礼之徒,寔繁其侣。金钱之税,悦以心竞。每于斋日,出置高座,数百千众,烧香散花,花虽盈积,牙函不没。
伽蓝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余尺,石基砖室。其中佛像,众宝庄饰,或铸金、银,或熔鍮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蓝。
伽蓝东南不远,有大精舍,石基砖室,高二百余尺。中作如来立像,高三十余尺,铸以鍮石,饰诸妙宝。精舍四周石壁之上,雕画如来修菩萨行所经事迹,备尽镌镂。
石精舍南不远,有日天祠。祠南不远,有大自在天祠。并莹青石,俱穷雕刻,规模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户充其洒扫,鼓乐弘歌不舍昼夜。
大城东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在昔如来于此六月说身无常、苦、空、不净。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又有如来发、爪小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诚旋绕,必得痊愈,蒙其福利。
六、纳缚提婆矩罗城
大城东南行百余里,至纳缚提婆矩罗城,据殑伽河东岸,周二十余里。花林清池,互相影照。
纳缚提婆矩罗城西北,殑伽河东,有一天祠,重阁层台,奇工异制。
城东五里有三伽蓝,同垣异门,僧徒五百余人,并学小乘说一切有部。伽蓝前二百余步,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基虽倾陷,尚高百余尺,是如来昔于此处七日说法。中有舍利,时放光明。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伽蓝北三四里,临殑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昔如来在此七日说法,时有五百饿鬼来至佛所,闻法解悟,舍鬼生天。说法窣堵波侧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其侧复有如来发爪窣堵波。
自此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殑伽河,南至阿逾陁国。(中印度境。)
○阿逾陁国
阿逾陁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谷稼丰盛,花果繁茂。气序和畅,风俗善顺,好营福,勤学艺。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大乘小乘,兼功习学。天祠十所,异道寡少。
一、世亲、胜受及佛遗迹
大城中有故伽蓝,是伐苏畔度菩萨(唐言世亲。旧曰婆薮盘豆,译曰天亲,讹谬也。)数十年中于此制作大小乘诸异论。其侧故基,是世亲菩萨为诸国王、西方俊彦、沙门、婆罗门等讲义说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临殑伽河岸大伽蓝中,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如来为天、人众于此三月说诸妙法。其侧窣堵波,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伽蓝西四五里,有如来发爪窣堵波。发爪窣堵波北,伽蓝余趾,昔经部室利逻多(唐言胜受。)论师于此制造经部《毗婆沙论》。
二、无著与世亲故事
城西南五六里,大庵没罗林中有故伽蓝,是阿僧伽(唐言无著)。菩萨请益导凡之处。无著菩萨夜升天宫,于慈氏菩萨所受《瑜伽师地论》、《庄严大乘经论》、《中边分别论》等,昼为大众讲宣妙理。庵没罗林西北百余步,有如来发爪窣堵波。其侧故基,是世亲菩萨从睹史多天下见无著菩萨处。无著菩萨,健驮逻国人也,佛去世后一千年中,诞灵利见,承风悟道,从弥沙塞部出家修学,顷之回信大乘。其弟世亲菩萨于说一切有部出家受业,博闻强识,达学研机。无著弟子佛陁僧诃(唐言师子觉。)者,密行莫测,高才有闻。二三贤哲每相谓曰:“凡修行业,愿觐慈氏,若先舍寿,得遂宿心,当相报语,以知所至。”其后师子觉先舍寿命,三年不报。世亲菩萨寻亦舍寿,时经六月,亦无报命。时诸异学咸皆讥诮,以为世亲菩萨及师子觉流转恶趣,遂无灵鉴。其后无著菩萨于夜初分,方为门人教授定法,灯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虚下降,即进阶庭敬礼无著。无著曰:“尔来何暮?今至何谓?”对曰:“从此舍寿命,往睹史多天慈氏内众莲花中生,莲花才开,慈氏赞曰:‘善来广慧,善来广慧。’旋绕才周,即来报命。”无著菩萨曰:“师子觉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绕时,见师子觉在外众中,耽著欲乐,无暇相顾,讵能来报?”无著菩萨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说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说妙法,义不异此,然菩萨妙音,清畅和雅,闻者忘倦,受者无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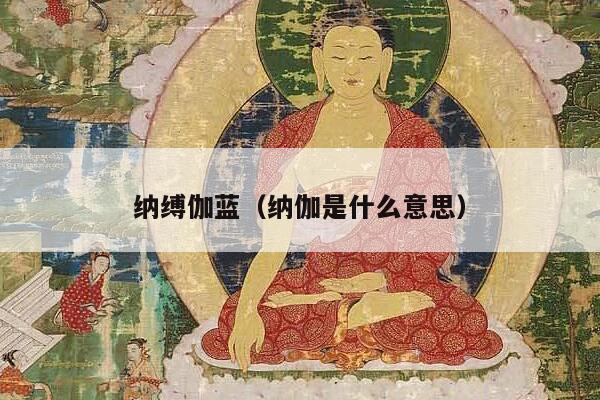
大唐玄奘
玄奘法师(公元602—664),俗家姓陈,名袆。河南陈堡谷(今少林寺西北)人,兄弟四人,玄奘最幼。二兄长捷先出家在东都洛阳的净土寺。玄奘十三岁也出家于这所寺院。
玄奘出家后,好学不倦,聪颖非凡,跋涉数地,遍学名家,在未西行之前,几乎已遍习中土之佛学。且拜谒之人多是名家大家,统鉴计卷,其辗转十三家如下:
所学地
师承
所学内容
洛阳·净土寺
景法师
严法师
涅槃
摄大乘论
去蜀途中
慧景 空法师(不详)
《毗昙》 《摄论》
成都
道基
宝暹
道振(志振、志震)
《毗昙》
《摄论》
《迦延》
相州
慧休
《杂心》 《摄论》
赵州
道深
《成实》
长安·大觉寺
道岳
法藏 僧辩之
玄会
兹论宗
《摄论》
《涅槃》
玄奘大师至蜀,多因前朝乱世,高僧多避居于蜀部。而前往蜀部的途中所遇的慧景,长于《摄论》,是声誉满京国的大德。
成都大德云集,玄奘受教于道基大师。道基曾受学于彭城。彭城是中国佛教毗昙宗之祖慧崇常居之处,慧崇虽已逝,但毗昙之学盛。道基便出于此门。
宝暹大师同慧景、智脱、道基并称“东都四大首座”,亦善明《摄论》。《续高僧传》卷十四云其“神志包总,高岸伦涛,谈论倚伏”。
道振的毗婆沙学,为当世名家。其学问于《迦延》,僧玄会曾学其门下。
玄奘法师在蜀中多学诸师,年龄尚未及二十五岁,于诸论造诣之深,博学之处,已是蔚然大观。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离蜀东下,在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毗昙》,自夏迄冬,各得三遍”。
在相州,受学于慧休大师。慧休大师(548—646),实乃三藏俱明,学问罕有人及的大人物。他初学涅槃名家灵裕法师,习《华严》诸经纶;往渤海从明彦法师习《成实论》,而明彦法师,史称之为“成实元绪”;明彦法师去世后又从志念学小论。志念法师是毗昙慧崇,成实明彦的弟子。慧休从灵裕法师入关,遇昙迁禅师学《摄论》。昙迁禅师先在北地学地论,后于建业,彭城学摄论,“史谓摄论北土创开白迁为始”;慧休又学于道尼,道尼为摄论宗祖真谛大师之弟子;从道洪律师学《四分律》,晚年从法砺讲律。广博精深之下,造《杂心》、《摄论》章疏,为其心得所在,玄奘从慧休学八月有余,自是受益汇深。
道深,志念之弟子,精擅《成实论》,玄奘从学《成实论》五聚之学。
贞观二年(628)初,时玄奘年约二十五,再至长安。
在长安期间,受学于道岳,法常,僧辩之,玄会诸家。
道岳,曾受学于僧粲,志念,智通,皆当世名僧。从真谛弟子道尼学《摄论》,又得智恺手记《俱舍疏》本,《十八部论》,于《俱舍》钻研至深,卓然名家。玄奘从学此论。
法常,昙延之弟子。
僧辩之,智凝之弟子。昙延和智凝都是摄论名师。
玄奘在中土所学的十三家,俱为名宿,而此时之玄奘学问之弘深,也是传于天下。法师学问风格偏重法相之学,这从所从学的老师中可以看出。十三师中,从学的《摄论》者就有六人,而立志到印度取经,也是志在取《十七地论》。对般若学问,玄奘法师未曾着意重视。十三师中,没有一个是般若名家。玄奘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寺中的明旷法师就是般若名家,但没有任何两人交往的文字记录。玄奘游川蜀,荆州,三论学者颇多,也未曾有闻有交涉。而玄奘初入长安,高僧嘉祥吉藏在京,玄奘未有请谒,可见学问重心偏颇。当然,其学虽不重般若,但未尝不知道般若。玄奘法师到了凉州,曾讲《摄论》,《涅槃》和般若,可见一斑。
未西行之前,法师学问已经规模弘大,绝非仅为一经一论之专家!
玄奘西行,旨在取《瑜伽》。
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秋,自兹西去,时年二十八。(据陈垣《书慈恩转后》年岁考证)。
这一路的孑然孤游和艰难惊险被后世传颂,一直到明末变成了《西游记》。玄奘法师途中高昌王,叶护可汗通告和护送,中途路经诸国,供给颇盛,远胜于当年“偷渡”出关的窘境。
贞观十九年春,玄奘归自西域。凡此十数年,其学问,事功,令誉,风度,绝人之毅力,博印度、西域诸国的隆礼。其造诣之深,声誉之隆,在印度无人可并,千古一人矣。
玄奘去印度,虽旨在取《瑜伽》之大论,但其学习不限于瑜伽诸宗,遇到名师必认真研学,无半点驰惫。前后在各处受学知名学僧约十五人,不知名者又有若干人,所记大致如下:
所学经论
所学地
传者
学习时间
《毗婆沙》
缚喝罗国纳缚伽蓝
般若羯罗(慧性)
月余
《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毗婆沙》
迦湿弥国阇耶因陀罗寺
僧称(一作胜)
二年
经部、《百论》、《广百论》
磔迦国
长年婆罗门
一月
对法 《显宗》、《理门》
那仆底国突舍萨那寺
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
十四月
众事分毗婆沙
阇烂达那国那伽罗驮那寺
旃达罗伐摩(月胄)
四月
经部毗婆沙
禄勒那国
阇那毱多
以冬半春
有部辩真论
秣底补罗国
密多斯那
半春半夏
佛使毗婆沙
日胄毗婆沙
羯若鞠阇国(曲女城)
跋达罗毗诃罗寺
毗离耶犀那
三月
瑜伽论等
摩羯陀国那烂陀寺
戒贤法师
五年
毗婆沙、顺正理
依烂那国
恒他揭多毱多(如来密)、羼底僧诃(狮子忍)
一年
集量论
南侨萨罗国
某婆罗门
一月余
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
驮那羯磔迦国
苏补底,苏利耶
数月
徵问瑜伽论
达罗毗茶国
僧迦罗国僧
正量部根本论、摄正法论、成实论
钵伐多罗国
某二、三大德
二年
婆沙等决疑
那烂陀寺西
般若跋多罗
二月
唯识决择论等
那烂陀附近杖林山
胜军法师
二年
以上这个图中是玄奘法师在印度有痕迹可寻的师承学习。其中,那烂陀寺作为古代中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玄奘法师于此居留和学习的时间最长。那烂陀寺是唯识学之中心,后渐修学习范围包括了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等无不笼及,玄奘在那烂陀寺主要从学于戒贤法师。
戒贤法师是法相大师,承传护法(唯识十大论师之一)的唯识之学,作为那烂陀寺最显赫的法相大师,戒贤学识之博,之深对玄奘的影响是显而见之的。玄奘后来在那烂陀寺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奠定自己在那烂陀的位置。戒日王于曲女城法会,邀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大乘,小乘,婆罗门众七千余人,这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曲女城辩论大会”。玄奘为“论主”称颂宣扬大乘佛法,做“真唯识量颂”悬会场门外十八日,竟无人敢发论难之。戒日王使大象施幢,玄奘高高乘上,宣告着一代佛门英才之无敌。大乘僧众称玄奘为“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佛徒则称赞玄奘为木叉提婆(解脱天)。十八国国王于会后都皈依在了玄奘门下。
玄奘法师意欲归来,戒日王挽留不住,和鸠摩罗王又邀请了十八国国王在首都钵罗那迦城连开七十五日布施大会请玄奘随喜。道俗两界到会者五十余万人。玄奘声望在印度之高,千古以来,唯此一人。这大概也是中国人在外国宗教文化界取得的最高成就,千古以来,唯此一人。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到了京城,这一年,玄奘四十四岁。
按照《旧唐书》所记“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可见太宗对玄奘之认可,随后“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富寺翻译”亦可见太宗对佛教及玄奘之支持。黄仁宇“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大约也是照着《旧唐书》比划出太宗的态度。但从种种蛛丝马迹来,怕未必是如此。
欲知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当然要看他对待佛教的言行,而对待佛教之言行和态度,亦是太宗对待玄奘之态度。
太宗皇帝与佛教之结缘,民间传以最盛的是借嵩山少林寺僧抗王世充事。武德七年,下旨僧法雅发京寺中骁捍僧人千余人充军伍,这大约是最典型的官民之利用关系。太宗讨伐王世充,用了僧人,等破了洛阳城,“乃废隋唐寺院,大汰僧人”。态度可见一般。
太宗李世民上位,是诛杀了兄长李建成后才顺利登基的。当时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徒拥护的李建成,而以王知远为首的道教徒拥护的则是李世民。贞观十一年(637),太宗下旨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贞观十三年,太宗找了个借口,把佛教领袖之一的法琳流放益州,法琳死于途中。
《大宋僧史略》不误悲伤的记载道:
“自唐有天下,初则佛法萎迟,盖李教勃兴,物无两大故也。傅奕上疏条释氏之愆,神尧不无其惑;次巡幸冬洛,太宗诏令僧尼班于道后。”
应该说,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太宗皇帝也修寺院。寺院修建的多少也是他们的态度之一。梁武帝时就修了许多,杜牧写“南朝四百八十寺”只是一斑而已。隋朝二帝曾大兴修寺。比之他们太宗修建的寺院多数目的性较强:
贞观三年设,是“忧五谷不登”;为太武皇帝造隆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此为“申孺穆怀”也;为战事中亡人设斋做道场,在旧战场建寺,以祭杀场之魂,如破薛举于扶风,建昭仁寺;败宋老生于吕州,设普济寺;灭宋金刚于晋州,设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败王世充于邙山,设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破刘黑闼于洺州,立招福寺;在率军征战高丽后,于幽州又建悯忠寺,这些都是为阵亡战士祈福而建,此种原因建寺院,自然和崇佛无关。
贞观二年时,唐太宗和身边的人聊起前朝风云,说到梁武父子崇好佛教,致使国破家亡,足矣为鉴,并道: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此话被收在《贞观政要》之中,为后人所鉴。
贞观二十年,太宗手诏斥萧瑀曰:
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为法门,倾帑藏以给僧袛,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并直言训斥萧瑀道:
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辩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
这话听完,估计这位梁武后人恐怕早就两股战战,头颈冒汗了。对崇佛误国相去不远,太宗皇帝是可以历历在目的,态度是可想而知。
太宗皇帝自认为自己是老子李耳之后,就是有心宗教,道教也要在佛教之前。太宗有事没事经常唠叨梁武,贞观二年,他和近侍聊天,道:如梁武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钮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缀,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以此可见,太宗估计对老子的好感也不太大,“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
翻译佛经(国家组识)也是崇佛的帝王们最爱做的事。远的不说,前朝的文、炀二帝便留有“译经八十二部,建寺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的数据。不仅如此,这父子俩人还有大量相关数据可觅;文帝“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区”;炀帝“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象十万另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区”。大约受了梁武、文、炀等帝王们崇佛亡国的刺激,高祖、太宗于此道都大大收敛。特别是太宗,修庙建寺多有目的,并不为佛,至于释经,贞观元年倒有一事。
高僧波颇自西突厥至于唐,太宗为他在大兴善寺立译场译经。
不过这事情多少不像太宗作风,所以有些说法。太宗在唐初外交上想远交近攻,一直找机会结交西突厥。突厥王叶护很是信崇波颇,太宗行事一向目的性较强,想来通过波颇法师外联西突厥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据说,太宗在兴善寺译场“礼意优厚”,但实际情况是:“昔符、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
事情如此!
前朝宏大的译经场面波颇是再见不到了,道宣在《续高僧传·波颇传》中记道:
其本志颓然,雅怀莫诉,因而构疾!
可怜的波颇恰逢此佛事未兴之前,大兴之后的空白档上。
我们的太宗皇帝在未见玄奘大师前也见过几个佛门大德,如回慧乘、明瞻等人。明瞻和尚“内通大小,外综丘坟,子史书素,情所欣狎”,和太宗兄谈的主要内容是“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兼“陈释门大极以慈救为宗”;慧乘等人也是博涉今古子史的人,太宗找他们聊天谈文史掌故的多,谈佛门之事只是附带而已。我们都还记得,太宗皇帝的诗词、翰墨都堪称“家”呢。
这时的玄奘既使名震西域诸国,但要太宗认真对待,估计远非正史所载那么简单。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回到故国。
玄奘回到长安。“迎者数十万众”,看来,虽隋、唐之间略纷乱几年,且太宗并不崇佛,民间崇佛基础倒还是雄厚的。据说当时从朱雀街到弘福寺的数十里间,道旁拥街拖儿带女来瞻仰圣容数十万众,烧香,散花不断。玄奘二十余匹马负经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如来真身舍利一百五十粒,金檀佛像七尊,于中国文化,中国佛教,此一天是绝对大事件!
这一年大唐的历史上,最浓墨的是“征辽”(高丽)事件。这是一场太宗精心准备的战争。玄奘急赴洛阳求得一见,太宗语近待曰:
昔符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
夸是夸了,仗还是要打。至于玄奘问译经的事,提出在嵩山少林寺译经。太宗不许,并道:
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降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
玄奘大师没少花言语,“固请乃许”。太宗便让留守的司空房玄龄安排,在西京弘福寺禅院开始译经。
玄奘学识广博,博通深沉,此种才华让太宗心里不舍,居然提出让玄奘还俗,当然有失所望。
翻译佛典,南北朝一直视此为国之要事。至若二秦之译事,门徒三千洋洋大众。隋唐洛阳兴善寺,上林院,义学沙门,多会于此,使译经盛事自长安鸠摩罗什,洛阳流支之后,再抵高潮。太宗此时于译事态度之冷淡,供事之简陋,对比实在是大。至于前面提到的波颇,孤单单的几个人,情景之冷清,今日再拒玄奘,也由此可见太宗对佛教之态度恐怕没有对玄奘本人感兴趣吧。
太宗让玄奘还俗辅政,并很认真的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此等要求,现在看来像个笑谈;比之当年梁武帝舍身入寺,恰成鲜明之对比。正史中所载的太宗对佛事冷淡,待玄奘之热情,也是可见一斑其中用心所在。
贞观二十二年以后,太宗征辽归来,英雄气概日渐消磨。年龄大了,对生死的问题多了留心,对佛教才慢慢多了留意。去世前,多次和玄奘说:“朕共师相逢间,不得广兴佛事”,这也说明大概他的即使有信佛也是晚年的事情了。
晚年和玄奘论金刚般若,听瑜伽大意,数次邀玄奘还俗辅政,对玄奘多方照顾有加看来,爱才大于爱佛。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唐太宗和玄奘法师在洛阳翠微宫畅谈佛理。五月,太宗竟然崩驾而去。使玄奘失去了一个对他的最大支持者。根据史实记载,唐太宗的突然崩驾和他长期的服用道士炼的仙丹有关。清赵《廿二史札记》直说,太宗皇帝就是因为服用丹药中毒而亡的,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和道士之间的关系。
其后的很长岁月中,在历史典籍里处处记载着唐朝的第三代帝王唐高宗一如既往的像太宗皇帝一样对待玄奘。
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师在玉华寺圆寂,时年六十五岁。高宗皇帝极为悲伤,罢朝数日,叹曰:
“朕失国宝!”
玄奘去世不久,高宗降旨,曰:
“玉华寺玄奘法师既亡,其翻经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旧例官给抄写,自余未翻者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其奘师弟子及同翻经,先非玉华寺僧者,宜放还本寺。”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译经便停止了,此后再无一人能够有如此力量宏兴佛事了。
玄奘法师小传之三 长路漫漫
进入伊吾,代表着玄奘偷越边关成功。
伊吾只有一所很小的寺庙,寺里的三个僧人都是汉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僧人听说来了汉人,来不及穿戴整齐,光着脚就跑了出来;刚刚从沙漠中走出来的玄奘,也是百感交集,两人相拥哭泣。
玄奘的西域之行异常艰难,他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严酷,还有各种人为的障碍。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很难坚持下来。
玄奘首先遇到的是高昌国王鞠文泰的强留。
高昌国笃信佛教,鞠文泰得知玄奘到达伊吾的消息后,派使臣强行把玄奘接到高昌。鞠文泰见到玄奘,如获致宝,殷勤供养。为留玄奘担任高昌国师,鞠文泰软硬兼施,用尽各种办法,甚至以遣送玄奘回大唐相胁迫;玄奘脱身无计,不得已只能以绝食表达自己誓要西行的志愿。
玄奘连续端坐了三天,滴水未沾,到第四天已是气息奄奄。鞠文泰终于妥协了,他既惭愧又恐惧,磕头恳求玄奘进食,并指日发誓同意玄奘西行。不仅如此,鞠文泰还与玄奘结拜为兄弟。两人约定玄奘取经归来时,在高昌停留三年。
玄奘在高昌停留了一个月,开讲《仁王般若经》。玄奘每次讲经前,鞠文泰都亲自手执香炉导引,并且跪在座前,让玄奘踩着他上座,日日如此。
鞠文泰为玄奘西行做了细致而周到的准备,“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巾、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他还给沿途各国王写了二十四封信,专门准备了给突厥叶护可汗的礼物,派官员欢信护送玄奘到叶护可汗衙。
从此以后,玄奘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了一个团队同行。
经过一些小国后,玄奘到了龟兹(今新疆库车县)。
在龟兹,玄奘和龟兹佛教领袖木叉毱多展开了一场佛法辩论,玄奘大获全胜。
因为大雪封路,玄奘在龟兹停留了两个多月。他留心观察,记录下了当地的许多风俗。比如他发现龟兹的管、弦乐器以及音乐、舞蹈比别的国家要好很多;那里人以扁为美,为了使头形长得扁薄,小孩子出生后要用木板箍扎着头⋯⋯
西域各国基本都是绿州国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之间,往往会有几百里荒漠,这种地方经常有强盗出没。
玄奘离开龟兹两天后,遇到了强盗打劫,强盗们动手之前,预分财产,争执之下竟然打了起来,以致自行而散。
玄奘继续往西走,穿过两个小沙漠,经过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到了凌山脚下。
凌山是葱岭的北端,险峭崎岖,峻极于天,冰雪终年不化,积而为凌。没有一个干燥的地方可以立足,烧火做饭只能把锅子吊起来,睡觉也只能躺在冰上。七天之后,他们才走出凌山。一行人因为冻饿而死的十有三四,牛马更多。玄奘有两个弟子也没有走出凌山。
继续西行。在碎叶城,玄奘受到了强盛的突厥王朝叶护可汗的友善接待。可汗不仅给了玄奘丰厚的施舍,还选派官员一路护送玄奘到印度边境。
经过几个小国家后,玄奘来到了位于西域中部的飒秣建国。
飒秣建国国力强盛,国人信奉拜火教,崇尚光明。这里没有佛教徒,虽然有两座寺庙,但没有僧人居住。在这里,如果有信仰佛教的僧人入住寺庙,当地人就会放火驱赶。
国王一开始对玄奘并不友好,可看在叶护可汗的面子上,还是接待了玄奘。玄奘抓紧机会,对国王讲经论法,一夜的功夫,就使国王开始接受佛法,高高兴兴地请求受斋戒,而且对玄奘也重视起来。
玄奘的两个徒弟不知当地风俗,到寺庙烧香礼佛,结果被一伙拜火教徒放火驱赶,险些丧命。
国王闻报大怒,把百姓召集起来,下令砍去放火者的双手。在玄奘的劝说下,改为从轻处理。自此之后,佛寺里有了僧人居住。
经过了几个小国家,玄奘进入帕米尔高原西部地区,穿山越岭,到达了突厥关塞铁门(今乌兹别克的南部)。出了铁门,玄奘到达了覩货逻国旧地。
覩货逻国旧地位于西汉张骞曾经到过的大夏。这里“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大夏在汉朝时是一个文化交流最集中的地方,人类历史上两大璀璨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朗文明在这里交汇,是东西方文化交错的地区。但是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分裂成二十七个小国家,它们都臣服于突厥。
玄奘在这里的活国(今阿富汗的昆都士)和缚喝国停留了一段时间。
在活国,玄奘竟然目睹了一场人伦惨剧。国君怛度设新婚的妻子和怛度的长子合谋毒死了国王,长子自立为设,娶继母为妻。古代许多少数民族有收继婚的习俗,父死娶继母,兄死娶嫂,都不足为怪。
在缚喝国的纳缚伽蓝,玄奘遇到了同样前来礼敬佛迹的印度小乘名僧般若羯罗,玄奘跟从他学习《毗婆沙论》,同时还跟另外两个有学问的僧人相从研习佛典。
自缚喝国南行,是揭职国。玄奘一行人千辛万苦,从职揭国东南进入了冰雪覆盖的大雪山,行进六百多里后,走进了重要的佛教圣地梵衍那国。
梵衍那国身处雪山之中,信奉小乘佛教中的“说出世部”。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就在这里。
玄奘稍做停留,往东又进入了茫茫的雪山,度过黑岭,到了迦毕试国。
此国城东有一座寺庙,叫质子伽蓝,传说是汉天子的儿子所造。异国他乡,玄奘如遇故人,倍感亲切,于是在寺中坐夏,停留了一段时间。
向东六百多里,再次越过黑岭,玄奘日思夜想的地方一—印度到了。
参考资料:
《大唐西域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玄奘西游记》 钱文忠著
董志翘《大唐西域记》前言
央视记录片《玄奘之路》 金铁木执导
四果的解释
四果的解释
(1).佛教语。声闻乘圣果有四,旧译依梵语称为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 罗汉 果。新译将前三果译为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仍其旧。 南朝 齐 周颙 《重答张长史书》:“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无疑其集佛。” 南朝 梁 沉约 《佛记序》:“非唯四果不议,固亦十地罔窥。” 唐 玄奘 《大唐西域记·纳缚 僧伽 蓝》:“伽蓝 西南 ,有一精庐。建立已来,多历年所, 远方 辐凑,高才类聚,证四果者难以详举。” (2). 宋 代民间教派名。 宋 陆游 《条对状》:“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易可测。伏缘此色人处处皆有, 淮南 谓之二禬子,两 浙 谓之牟尼教, 江 东谓之四果。”
词语分解
四的解释 四 ì 数名,三加一(在钞票和单据上常用大写“肆”代): 四方 。四边。四序(即“四季”)。四体(a.指人的四肢;b.指楷、草、隶、篆四种字体)。四库(古籍经、史、子、集四部的代称。亦称“四部”)。四 君子 果的解释 果 ǒ 某些植物花落后含有 种子 的部分:果实。果品。果木。 结果 (a.结出果实;b.事情的结局或成效)。 结局,与“因” 相对 :因果。 成果 。 坚决:果决。果断。 确实,真的:果真。如果。 充实 ,饱足:果腹。
《大唐西域记》卷一 三十四国(5)
○纥露悉泯健国
纥露悉泯健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
西北至忽懔国。
○忽懔国
忽懔国周八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
西至缚喝国。
○缚喝国
缚喝国东西八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北临缚刍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其城虽固,居人甚少。土地所产,物类尤多,水陆诸花,难以备举。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一、纳缚僧伽蓝
伽蓝内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余,杂色炫耀,金石难名。又有佛牙,其长寸余,广八九分,色黄白,质光净。又有佛扫帚,迦奢草作也,长馀二尺,围可七寸,其把以杂宝饰之。凡此三物,每至六斋,法侣咸会,陈设供养,至诚所感,或放光明。
伽蓝北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金刚泥涂,众宝厕饰。中有舍利,时烛灵光。
伽蓝西南有一精庐,建立以来,多历年所。远方辐凑,高才类聚,证四果者,难以详举。故诸罗汉将入涅槃,示现神通,众所知识,乃有建立,诸窣堵波基迹相邻,数百余矣。虽证圣果,终无神变,盖亦千计,不树封记。今僧徒百余人,夙夜匪懈,凡圣难测。
二、提谓城及波利城
大城西北五十余里,至提谓城。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余三丈。昔者如来初证佛果,起菩提树,方诣鹿园。时二长者遇被威光,随其行路之资,遂献麨蜜,世尊为说人天之福,最初得闻五戒十善也。既闻法诲,请所供养,如来遂授其发、爪焉。二长者将还本国,请礼敬之仪式。如来以僧伽胝(旧曰僧祇梨,讹也。)方叠布下,次郁多罗僧,次僧却崎,(旧曰僧祇支,讹也。)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窣堵波。二人承命,各还其城,拟仪圣旨,式修崇建,斯则释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
城西七十余里有窣堵波,高余二丈,昔迦叶波佛时之所建也。
从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锐秣陁国。
○锐秣陁国
锐秣陁国东西五六十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
西南至胡寔健国。
○胡寔健国
胡寔健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多山川,出善马。
西北至呾剌健国。
○呾剌健国
呾剌健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五六十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西接波剌斯国界。
从缚喝国南行百余里,至揭职国。
○揭职国
揭职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硗确,陵阜连属,少花果,多菽、麦。气序寒烈,风俗刚猛。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大雪山
东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山神鬼魅,暴纵妖祟,群盗横行,杀害为务。
行六百余里,出睹货逻国境,至梵衍那国。
○梵衍那国
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势邑居。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岩。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马。气序寒烈。风俗刚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逻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自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输诚,竭心宗敬。商估往来者,天神现征祥,示祟变,求福德。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

本文链接:https://www.sjxfo.com/bk/xin/4490.html
转载声明:本站发布文章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


网友评论